贵州文化老人丨读《播雅》诗集叙题、按语劄记
文章选自张祥光所著《读史集稿》,本书是以业已刊发的多单篇文章汇合编就的文集。就学科而言,以史学为主,兼及其它;就时间而论,以古代为主,兼及近现代;就空间来说,以贵州为主,兼及全国。时限长、区域广,涉及之人、事多。立论精当,史料翔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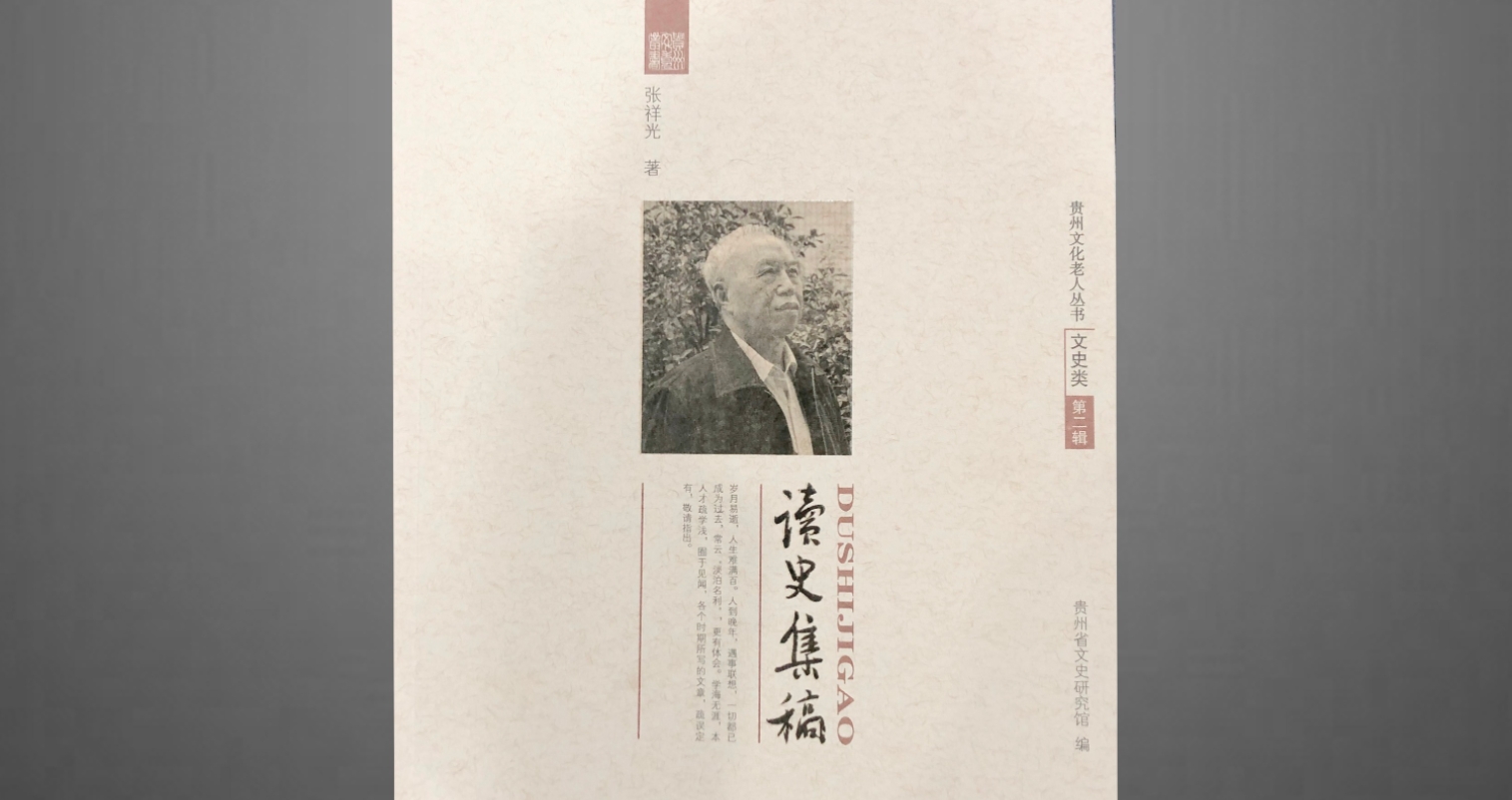
1841年,大学者郑珍编纂完成了《遵义府志》。之后12年,又在湖北布政使唐树义的资助下,编刻成《播雅》二十四卷。《播雅》一书收集了当时遵义府属四县明清两代220人诗作2300余首,为保存乡梓文献作出了重大贡献。
郑珍在收集、编纂、整理《播雅》诗集中,写了叙题和不少按语。这些叙题有对作者的背景介绍,有对史实的纠正,有对风俗、掌故的叙述,这对治地方史志来说,史料价值颇高。可以说,是郑珍在学术上的又一成就。
一、在人物方面对史实的订正
柳宗元未到过播州
柳宗元未到过播州,在今天已成定论。但在贵州历史上,却有过存疑。程生云写的《愚溪书院》一诗,就肯定了柳宗元未曾来过播地,“柳子何尝至播州,只因播土仰高流”。但万历时任职绥阳的知县,确说柳宗元到了播州。唐时,播州治所曾一度设在今绥阳。万历二十九年,平定杨应龙叛乱以后,詹淑为绥阳知县,他在愚溪书院刻碑记事,认为是柳宗元来播州后所建。
在《播雅》收录此诗条下,郑珍写了一大段按语,“书院以绥阳县西二十里大溪源,中祀唐柳子厚。……詹淑为首设绥阳知县,其作碑记云:治西有儒溪(即愚溪)书院遗址,佥谓昔柳公所建,则此书院之有,当不始于明矣。淑又云:有耆年孟元者,公之后世,藏公遗帖,昔有见者,今无存矣。因召见元,询其始末,谓公实乾符三年入播,世传如此,似非无因。遂捐资补葺旧宇,择近院田地三十亩,授元为业,并量免杂差,俾世守祠祀云云”。郑珍在引了这一段碑文后,批驳说:“柳子之不至播,断然无疑。孟元谓乾符三年(876年)入播,子厚徙柳州在元和十年(815年),后四年遂卒,卒后五十七年始为乾符三年,其语益荒诞无据。”郑珍从柳宗元贬柳州后的事迹考证,指出其荒诞之由。
颠仙是杨斌
郑珍按语对旧志乖错,纠正颇多。在《颠仙七首》写的叙题中说:“旧《府志》书杨颠仙云:名道凝,颠仙其自号,又号神霄散吏。《通志》改书张颠仙,世不审确为何姓。珍按:颠仙,实即播州宣慰使杨斌也。……《通志》误为张者,颠仙有诗刻郡治东桃源洞,俗悉谓是张三丰书,因是附会张姓耳。”
对竹王墓的否定
《播雅》卷八有李樵庚诗七首,其一《夜郎箐》有“竹王旧墓何从识,太白诗魂不可招”。郑珍对此诗写的按语说:“夜郎箐在桐梓治北三十里,上有祖师观。竹王墓在治南五里牛心山,额曰‘汉竹王墓’,相传即竹王父子之坟。余验其墓,石椁颇广大,两墙刻花草、人物,率纤俗,无汉人墓刻古雅气。其人并是苗装,或唐宋间土酋墓也。”
郑珍经过实地考察,否定了是汉竹王墓的传说。他认为,可能是苗族人之墓或是唐宋土酋之墓。
二、地名、水系的辩误
郑珍在整理《播雅》诗集所写的按语中,有不少是对地理位置、山川水系的辩误。
《播雅》卷一程生云《尹公讲堂》一诗中,郑珍按语指出,“《明史》于桐梓犹云,以绥阳旺草地置,可见后人不识地理;谓唐之讲堂在今旺里,大误”。这里一是批评了清代大学者张廷玉、王鸿绪等编纂《明史》对桐梓、绥阳两县地界张冠李戴的错误;二是尹珍讲堂即“务本堂”在今正安新州,与绥阳旺草南辕北辙,两地相隔甚远,而绥阳知县詹淑谓“余修旺草公署据地得碑,题曰‘汉尹珍讲堂’”。所以,郑珍批评詹淑所称“唐之讲堂在今旺里(旺草)”是极大错误。
在《播川废县》《愚溪书院》等诗中,郑珍所写按语对播州治所历史的变迁可以得知梗概。大约唐时,播州初设治所在今绥阳旺草。杨端入播后,遂治白锦堡,至宋大观年间,一直在今遵义县境之白锦堡。宋宣和年间,又迁置今桐梓之鼎山城。从播州治所的变化说明,杨氏据有播土以后,在宋代杨氏内部的斗争是很激烈的。
郑珍还在《播川废县》一诗的按语中,指出了《蜀志》的两点错误。一是,“播川废县,即鼎山废县也,在桐梓治南十里鼎山上,旧《蜀志》谓在县南三里,误也”;二是,“太原杨端入白锦,复播州,遂治白锦堡,即令郡南三十里,俗讹称之懒板凳也。《蜀志》云,在綦江县南八十里,并不确”。
在诗集中,有几处按语是对乌江水系的考辨,对乌江名称的变迁交待很清楚。这与郑珍、莫友芝所编纂的《遵义府志》中,有关乌江水系的叙述比较,更加简明。郑珍在《播雅》卷九《晓渡乌江》一诗的按语中指出,乌江即《水经》之延江,在唐或谓之邗水,或谓之琊川,或谓之湖江。乌江之名始见《元史·文宗纪》,而《李德辉传》言“尝梦主乌江”。在至元十七年(1280年),始称乌江。他又指出,乌江“源自威宁东北山,经毕节曰七星水,大定曰六归河,黔西曰鸭池河,修文曰陆广河,入遵义始称乌江”。
若按郑珍在诗集中《二郎滩》一诗所写的按语,鳛水县之鳛简化为习,是值得商榷的。他引桑钦的话说:“鳛部水、安乐水,同是今源自仁怀县北四百里之九倒拐……此水自高洞以下,土人皆名鳛水。水产鳛鱼,为他水所无,古于古地名鳛,其水即名鳛部水。”可见,郑珍的考论说明地名系因流经此地的水域特产——鳛鱼而得名,今地名去掉了鱼字旁,就失掉了地名由来及取名的原意。
我们还可在郑珍所写的按语中得知个别物种的灭绝,以及特有的郡俗及黔北文化与巴蜀文化的密切关系。如郡俗,他在《播雅》卷八《田鼓歌五首》的按语中写到,“郡俗尚饮咂酒,乡村燕劳十九用之”。清代李宗昉的《黔记》、吴振棫的《黔语》都有关于少数民族饮咂酒的叙述,至今仡佬族、苗族还有饮咂酒的习俗。李宗昉在《黔记》中说:“咂酒,一名重阳酒,以九月贮米于瓮而成,他日味劣。以草塞瓶颈,临饮,注水平口,以通节小竹插草内,吸之,视水容若干征饮量。”清代,今遵义地区仡佬族、苗族分布较多,他们的咂酒习俗也影响着其他民族。所以,郑珍说,“郡俗尚饮咂酒”。
总之,郑珍在编纂《播雅》诗集时所写的叙题、按语为治地方史志者提供了不少极有价值的史料,值得认真研究。
作者简介:
张祥光,贵州桐梓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学会理事,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副秘书长,贵州省史学会顾问、贵州地方志研究会顾问。著有《贵州古代史》(合著,任副主编)、《贵州近代史》(主编之一),参与编写《贵州通史》五卷本中第一卷魏晋至五代十国、《贵州省志·政府志》《贵州省志·文史馆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