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sheng阅读丨 作家冉正万:我就是那条鱼


【冉正万,贵州余庆人。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银鱼来》《天眼》《纸房》《八匹马》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的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曾获花城文学奖新人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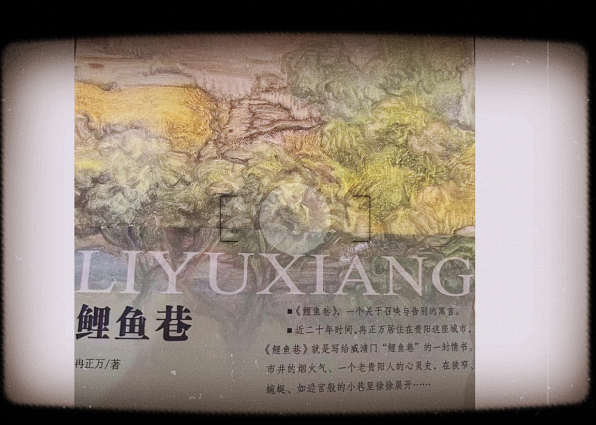
新视角:关注贵阳小街小巷
一条市井小巷,一个关于召唤与告别的寓言,一封写给贵阳老巷的情书……近日,收录了贵州作家冉正万10余篇作品的短篇小说集《鲤鱼巷》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老巷子——鲤鱼巷,冉正万不下百次来过这里,或路过或来此消费,甚至没有目的在里面闲逛。他一向擅长贵州乡土民俗题材,因创作短篇小说《鲤鱼巷》,首次将视角转向自己生二十多年的城市。冉正万说,贵阳的小街小巷很有特点,生活气息浓郁,烟火气十足。
《鲤鱼巷》为了追溯老巷子的历史,冉正万不仅聆听老居民讲述鲤鱼巷,还查找了相关史料。很多年以前,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山上泉水流到此处,人们造田种水稻,水田里鲤鱼活蹦乱跳,于是取名鲤鱼田。村寨形成后,改名鲤鱼村。再后来城市将其包围,稻田不见踪影,农村迹象宵遁,鲤鱼村变成鲤鱼街。老人说,八十年代初还有几块稻田。如今,老街两侧的房子或高或低,或大或小,像一条老鲤鱼的鳞片。“现在的人很难想象鲤鱼巷一带发生过多么大的变化。”
评论者李巽南说,《鲤鱼巷》描绘了贵阳老巷子原汁原味的店铺街貌、老巷居民的原生态生活、以及市井烟火中的精神追求,也展现了旧城拆迁改造给原住民生活及心理带来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作家冉正万的眼中,是一种顺其自然的正常变迁,一如鲤鱼巷从鲤鱼田、鲤鱼村演变而来的变迁,是时代变化、文明进程的缩影。
该短篇小说集收录了作者近5年发表在全国各大具有影响力的文学刊物上的作品,包括《鲤鱼巷》《烧舍利》《屋檐童子》《宇宙琴弦》等10余篇短篇小说,每篇作品都藏着不同的个人世界,以独具特色的黔地文化、细腻鲜活的人物刻画、贴切生活本真的内容呈现,以及人性和现实的深层挖掘,聚焦对信念、良知的坚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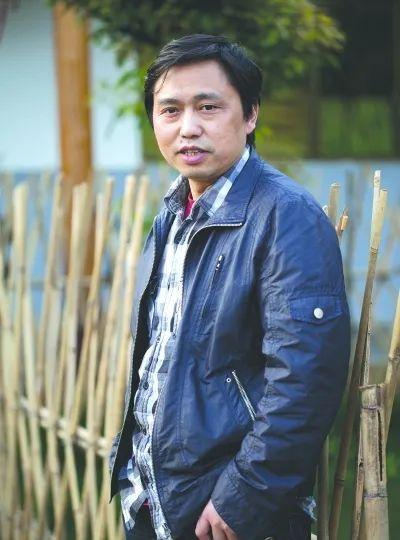
与当下一些文学作品在描写乡村消失、城市变迁时暗藏的哀伤情绪不同,冉正万认为凡是“新的来、旧的去”,都是历史的正常进程,变化寓意着新的生机,作家应该跳出个人情感色彩,以客观的视角看待乡村和城市的蝶变与发展。比如在冉正万的黔北老家余庆县,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打工,原来的村子虽然空壳了,当地的野生动物数量和种群却越来越多,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三百年前,那里没有人烟,三百年后如何现在不知道。把自然还给自然,也好。
《人民文学》卷首语中评价该小说:冉正万的作品立足于西南山地的文学世界,写作手法极其鲜明,作品里的现实性来自于客观的自然地理环境,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深深影响着他的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他的“理想主义世界”能够在作品里得以体现。
 (冉正万《鲤鱼巷》新书发布会现场照片)
(冉正万《鲤鱼巷》新书发布会现场照片)
创作源泉:手中的书本 耳朵里的故事
“故事不能生造,灵感来自于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深度体验。”冉正万说:“短篇小说最利于留住稍纵即逝的灵感。”
冉正万出生于贵州余庆县一个叫黄土湾的山村,从小酷爱阅读。
一个冬天,还在上初中的冉正万借到了《三国演义》,屋子里烟熏火燎,家里穷,不好点煤油灯。提了个小板凳坐到雪地看,被跌宕起伏的故事吸引,浑不觉身上寒冷。
一个炎热夏夜,家人让他守水渠,他借着亮堂堂的月光忘情地啃着厚厚的书,水渠里的水什么时候被人偷了都不知道。上高中后,他省吃俭用,买下的第一本书是作家金河短篇的小说。这是他第一次读到当代作家的短篇小说。
除了阅读,冉正万从小也喜欢听故事。无论是听村民们用山歌、花灯调唱出的人间悲喜,还是行走南北听不同人回忆往事,各式各样的故事对冉正万都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专注于故事对他来说就像吃饭一样平常。曾经作为地质队员在田野中风餐露宿的人生经历,更馈赠给他无数的奇闻异事。他想把其中有趣的、难忘的故事记录下来,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热的影响下开始了文学创作。
从《银鱼来》到《鲤鱼巷》,为什么选择用“鱼”来表达?冉正万说:写《银鱼来》的时候,是因为在野外的时候,看到山洞里的银鱼是透明的,它很娇弱,但也是很伟大的生命,就像每个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我们也是透明的,我感觉“它”就是我,我就是“它”,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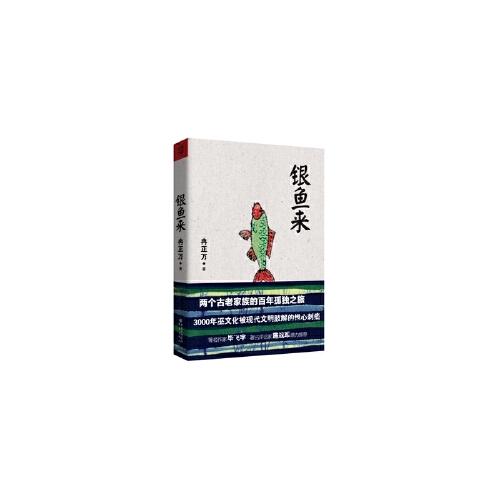 完整节目内容摘要:
完整节目内容摘要:
4:40 作家写作都是“自然收集”
6:45 有的东西正在失去也正在到来
8:10 看得见、有感情,才有话可说
14:15 雪地里看书的少年
16:16 用文字还原梦境
17:05 阅读时会用小卡片记录下来
30:50 我就是那条鱼
34:30 第一个短篇小说《高脚女人》
40:21 未来会用更多时间去写贵阳的小街小巷

《好sheng阅读》主持人大方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