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静文学丨一位诗人的人文基座与诗性的力量
一位诗人的人文基座与诗性的力量
——简评《欧阳黔森诗选》
欧阳黔森的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诗歌、影视剧等,可谓非常广泛。众所周知,大多数人可能认为他的主要成就体现在小说和影视作品上,在我看来其实不然,他的散文、报告文学和诗歌创作也成绩斐然。现在他的诗集《欧阳黔森诗选》在朋友们共同的期待中闪亮登场了,为他的文学人生又增添了绚烂的笔触。纵观欧阳黔森这四十年的文学生涯,我想《欧阳黔森诗选》就像其文学版图上精美的花边,点缀着装帧着他的文学人生,我便有了妄言几句的冲动,以期从我的角度,谈谈这本诗集在其文学版图上所彰显出来的一位诗人的人文基座与诗性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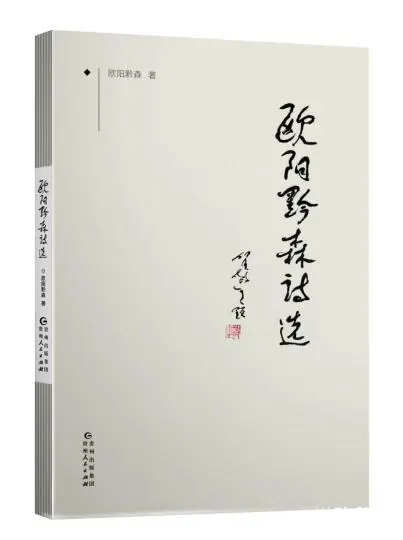
1815年的春天,二十岁的英国诗人济慈站在教室外的花树下,老师问他喜欢什么样的诗歌,他沉默片刻,看着头顶微微颤动的花枝说:“诗歌,应该像树叶长在树枝上那么自然”。济慈的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诗歌的结构、气息上要自然,要通畅,更应该理解为诗歌的生成要有内在的基因,要有思想和情感的合理性,就像树叶长在树枝上一样自然。
2024年6月25号,在青海举行的“第五届昌耀诗歌奖颁奖典礼暨吉狄马加诗歌跨界创作研讨会”上,大多与会诗人和评论家都围绕吉狄马加的诗歌文本作精细的解读,由于我2012年在百年新诗大型纪念专题“世纪访谈”时给马加做了13000字的长篇访谈,对他的整个创作与诗歌活动有更多的了解,所以我思考的角度则是吉狄马加为什么会成为吉狄马加,以期从文本背后,从一个更为宏阔的角度,来溯源一位诗人的人文基质,来解读由此生长出来的诗歌文本。
我的发言以《在诗性背后……》为题,从文本发生学这个角度,来研读一位诗人的诞生与人本和文本的互为关系,以期解读诗人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思考,为什么具有这样的情结,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话语方式,为什么是这样的美学形态等话题。
记得2009年至2011年我与杨正江创编整理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时,写了《试述亚鲁王的英雄史诗属性与独特品质》一文,文中我提出了“民族性格的生成史”这个概念,从一个民族性格生成的角度,从人文基因的层面,阐释了一个民族的性格与其命运的互为生成关系。
在我看来,这个关系不仅仅是简单的逻辑关联,而是一种更加内在更加富有人文基质的心灵与文本的互为关系。显然这样的关系同样在一位具体的作家、诗人身上生长着、演绎着,具体表现为一种人文基因的内生性基质。
此刻也许朋友们想,我为什么在言说《欧阳黔森诗选》之前,要从济慈的那句名言出发,要谈到吉狄马加诗歌研讨会我的发言,要回忆我在创编整理《亚鲁王》英雄史诗时谈到的“民族性格的生成史”这些话题,其实,我是想透过文本,从语言的背后来发掘一位诗人的心灵、格局、情怀、大爱、担当及由此形成的人文基座,来阐释一位诗人的诞生及人本与文本的相互生成,以期获得对诗人的人本与文本的双重互证和彼此的朗照。只有这样,我们对一位诗人文本的解读才是客观的、真实的、立体的、有效的、内在而富有力量的,既是对诗人的尊重,也是对文本的尊重。我们拥有什么样心灵,就会拥有什么样的人文基质,就会创作出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就像什么样树枝就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树叶一样。其实,这是一位作家严格区别与其他作家的重要的内在标识,是一位作家的人文基座。
我与欧阳黔森认识近30年了,对他的整个文学生涯与创作成有大致的了解。尽管他的著作颇丰,方方面面都成就非凡,但我认为最能代表他艺术才华与文学成就的其实是他的短篇小说。1999年他在《当代》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十八块地》之后,短篇小说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接二连三地在《当代》《十月》《人民文学》《中国作家》等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像《断河》《敲狗》《丁香》《血花》等脍炙人口的作品,获得了广泛的赞誉,并获得短篇王的美誉。其中,《断河》在2004年入围“第三届鲁迅文学奖”,《敲狗》在2006年获得“蒲松龄短篇小说奖”榜首。他的小说中,巧妙地运用了很多诗歌,并在小说中有了点睛之妙,在其众多的小说中,都见端倪。由此,我有理由认为,能写好诗歌的人,一定能写好短篇小说,诗歌的凝练、简洁,正与短篇小说创作的精髓异曲同工。
欧阳黔森出生在贵州铜仁,他自幼受到诸多红色故事的熏陶,自幼形成一种崇拜英雄的人生情结,这种情结可以说影响了他一生的创作,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影视作品,无不渗透着他对英雄的崇尚。他1984 年参加工作,是贵州地矿局103地质大队的一名地质队员,历任组长、项目负责人。这是一份异常艰辛的工作,用自己的双脚,翻山越岭,在崇山峻岭中寻找矿藏。这样的经历,使他与祖国的大自然有着特别的情感和挚爱,这也是他人生中另一个嵌入灵魂的重要情结。从欧阳黔森整个创作历程来看,我们鲜明地从他对英雄的崇拜与对大自然的热爱中提炼出“敬畏”这个异常重要的关键词,这是一个萦绕欧阳黔森几十年创作生涯的一个关键词,对英雄的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大自然的敬畏,并由此形成了一位作家的格局、情怀、大爱、担当的人文精神与文学品格,从而坚实地构成了一位作家基于历史道义与人文良知的文学创作的最本质的人文基座。
欧阳黔森的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从1985年在《杜鹃花》上发表了诗歌处女作《晨曲》出发,开启了他的诗歌创作之路。从诗歌创作出发,走向文学之路,应该是古今中外绝大多数诗人、作家走向成功的路径,一是因为诗歌本身的独特魅力,二是因为诗歌创作对于培养自己的感知力、淬炼自己的语言能力都有很大支撑,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黔森的诗歌创作,对其整个文学和影视剧创作所取得的非凡成就显然功不可没,有着重要的意义。
我用三个晚上的时间细读了《欧阳黔森诗选》,感概颇多。诗集由《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俄罗斯诗抄》《新疆行》《缘象花一样绽放》《民族的记忆》《共和国不会忘记》《地质之恋》七个组诗与长诗《贵州精神》以及《旗树》《我知道你走了》《一句格言》《李彬颂》四首短诗构成。在我的阅读经验与期待中,我总是渴望在文本的背后,触摸到诗人心灵的温度、精神的质地、诗性的力量,只有文本具有了这些人文内核的元素,语言才能获得灵魂的支撑,文本才具有应有的质地与重量。
在我看来,心灵是诗人、作家最大的才华,只有心灵,才能让文本获得灵魂的温度、思考的重量、充满纹理的质地、诗性的力量。所以我常说我们只有把心灵昼夜打开,再打开,我们才能听到万事万物的声音,才能听到神奇的声音,我们写下的文字才有可能具有一点点价值和意义。
阅读《欧阳黔森诗选》似乎是轻松的,因为他的语言朴素、真切、简洁,总是在不动声色的叙述,自自然然就流淌进读者的内心。阅读中,我的思绪不断被激活,每读一首,都要掩面沉思,我强烈地感悟到文本的每一个意象,每一个思考,完完全全是从欧阳黔森体内生长出来的,都是从他的血汁渗透出来的,都是他血液的喧响,人本与文本获得了一种双重的互证,而且这样的互证是一种肉体、精神、文本三位一体的彼此构建、相互支撑、共同呈现的诗学存在。显然,这样的诗学存在是坚实的,是灵魂的,是诗性的,并成为一种诗歌生成的有效路径,这就大大提升了诗歌文本的精神纯度与诗性的力量。
诗集开篇是组诗《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这组诗歌我几年前就精读过,当时我就认定这组诗歌是欧阳黔森的代表作,无论题材上体现出的格局与情怀,还是饱满与炽烈的情感,都完全是从他体内自自然然生长出来的,是真实的生命体验所分泌出来的诗歌,这是一部作品最为核心、最有价值、最具温度、最富质感、最有重量的的部分,这是一位诗人作家的人文起点与艺术逻辑,这就从本质上远远地把那些强说愁的文字,那些无病呻吟的情绪从心灵上严格地剔除。
从诗歌本身的意义上说,认知上的嫁接、文本上的拼贴、语言上的游戏如果成为一种时尚的话,那么大量“假花”一样矫情的文本将会充斥着诗歌现场,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对心灵的背叛,对文本的远离。哲学家维特根斯坦非常强调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忠实于具体的场景和细节,这就为我们的诗歌回到心灵,回到文学的本身,具有本体性的哲学支撑与直接的现实意义。维特根斯坦强调学习应该是一种实践性的活动,强调语言和语境的重要性。因而,从心灵出发,忠实于自己的灵魂,忠实于真实的情感体验,这才是文学之根本,才是文学的有效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黔森这些从心灵出发,从敬畏出发,从真实情感出发的文本,才是真正具有文学力量的文本。我们先来看看具体的文本。
沿着套色分明的中国版图
向西、向西
跨跃横断虚空的断裂
隆起与沉陷
构成大手笔的写意
向西、向西
那儿有狂风般骠悍的骑手
那儿有风吹草低的原野
那儿有高不胜寒的雪山
世界屋脊上
雄性十足的头颅
昂然挺立
呈银色衬出你的威仪与深邃
你白发苍苍
但双眼仍然年轻
一泻千里的两道目光
掠过沧桑沉浮的版图
严厉而慈祥
只有这博大而神奇的目光
才有着生命力的色彩
一道黄色
一道蓝色
于是东方古老的江河民族
生生不息地享受你的严厉与慈祥
至今——五千年
向西 向西
去骑一骑狂风般骠悍的骏马
去看一看风吹草低的牛羊
去摸一摸冰凉的世界屋脊
去吧!男儿要远行
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
——《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
在西沙
分不清海水与天空
哪个更蓝
在西沙
分不清人间与天堂
哪个更好
在西沙
天像海一样蓝
海像天一样碧
在西沙
浪是风的魂
风是浪的魄
风起浪卷
水的肌肤上绽开花朵
——《西沙群岛》
只有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的人,才能从胸腔里涌出这些纯美而充满着挚爱的的文字,而这种爱是源自心灵深处,尽管不动声色,但却汹涌着力量,让人们在赞美大好山河的同时,自然激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这样的心灵与文本的完美结合,无论是古今,还是中外,既是一种艺术创作的有效路劲,更是一种文本生成的典范,这也是我在前文谈到的,为什么吉狄马加会成为吉狄马加,为什么欧阳黔森会成为欧阳黔森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欧阳黔森没有炽烈而纯粹的大爱,没有对这片土地源自灵魂深处的敬畏,就不会有如此纯净而汹涌着力量的诗句。
人本与文本的相互结构、彼此照耀、共同呈现,是文本获得情感真实的一个重要前提,更是文本的品格与力量的重要支撑与完美呈现。尽管文本与人本常有相悖的情形,这从更高的意义上对文本情感的真实性提出了更加高级更加纯粹的要求,同时也彰显出这种人本与文本相互生长的创作,才能真正具有文学的力量与诗性的品格。
《俄罗斯诗抄》我认为同样是欧阳黔森的代表作之一。在世界文学中,我国应该是受苏联文学影响最大的国家,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苏联诞生了一大批灿若星河的文学大师,列夫·托尔斯泰、肖洛霍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文学巨匠,在我国更是家喻户晓,深得我国诗人、作家及读者喜爱。显然,正是由于对苏联文学的挚爱,欧阳黔森在俄罗斯访问期间,以一位诗人保有的敬畏之心和织烈的情感写下了组诗《俄罗斯诗抄》。我们再看看《在托尔斯泰庄园》的文本。
去他的墓地
要穿越一片森林
小路上冰雪洁白无瑕
每留下一步脚印
我都小心翼翼
两旁的树们都伸出手
捧着朵朵冰花
显得分外肃穆
像是在迎接我
参拜托尔斯泰公爵
又像是告诉我
不要随意打扰公爵
在这样的肃穆中
我只想在这位巨人的墓碑前
肃立,鞠上一躬
这是诗人拜访列夫·托尔斯泰庄园写下的诗句,不远万里,来到托尔斯泰的庄园,就为了向敬仰的大师鞠上一躬,诗人的内心,同样涌动着难能可贵的敬畏之心,正是这一份敬意与挚爱,让欧阳黔森面对神一样的文学巨匠,获了一种神圣的灵感,写下了这些充满虔诚与敬畏的诗句。我们在来看看下面的诗句:
没见过肖洛霍夫写过诗
可是,在这诗一样美的顿河
肖洛霍夫史诗般地存在
很难想象,没有肖洛霍夫的顿河
很难想象,顿河没有肖洛霍夫
顿河与肖洛霍夫像诗与远方
母亲与游子,永远的
必然的分不可离
如果说,美有千万种存在
那么,没有比凄美更令人刻骨铭心
肖洛霍夫的一生
如果说像鲜花一样灿烂
没有人怀疑这花的颜色红似火、艳如血
花朵,似乎永远残缺
花瓣的伤口分外灼目
我们看到的依然是虔诚、依然是敬畏,依然是这些关键词穿起来的心灵基因与人文基座,依然是活生生地从欧阳黔森体内生长出来。诗人首句就巧妙地书写了肖洛霍夫“顿河史诗”的文学价值,语言真切、朴素、自然,不动声色的叙述浸入心扉。我们再来看看为普希金写下的诗句。
站在你的脚下
抬头仰望着你
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
在圣彼得堡
在莫斯科
我至少看见十多座
你的雕像
每一次,我都会停下匆匆的脚步蹑足注目
在俄罗斯广阔的土地上
只要有你站着的地方
那个地方便会神圣起来
令人肃然起敬
——《在普希金雕像前》
“只要有你站立的地方/那个地方便会神圣起来/令人肃然起敬”,显然,同样是敬畏,同样是深深的爱,同样彰显了诗人人本与文本互为生成的双重见证与独特魅力。
我们再来看看组诗《新疆行》
来到楼兰
记忆最深的
并不是残垣断壁
以及,黄沙滚滚
千年的你
千年的存在
依然是我想象的源泉
有时候,我的臆想
像生长了翅膀
飞回千年前的楼兰古国
那是你美丽的家园
那时候
楼兰的天空
一定很湛蓝
那时候
罗布泊的水一定很清凉
那时候
你一定在孔雀河的
胡杨下
翩翩起舞
不可想象
这样的美丽时刻
是怎样戛然而止
可感觉的
只是你的妩媚
在老去的岁月中
仍然,风情万种
不难想象
你的眼睛
曾有蓝天一样的颜色
不难想象
你的身姿
曾有杨柳一样的婀娜
你躺在那儿
满怀岁月的痕迹
只要是见过你的人
无不唏嘘
千年的你
万年的胡扬
两样的伤感
一样的结局
——《楼兰姑娘》
楼兰是我国辽阔疆域和悠远历史的一种象征,对楼兰的赞美与感伤,寥寥数语,内心的伤感无以言表,同样是对这片土地源自内心的热爱,同样是真实情感的诗意彰显,同样是人本与文本的相互生成的彼此照耀。
我们再来看看组诗《缘象花一样绽放》
月牙儿弯弯
一头挑起,你的羞涩
一头钩出,我的胆怯
月光朦胧,夜色袭人
乍暖还寒梨花雨
你的脸,梨花一样白
我的心,梨叶一样青
……
这时,总是月满枝头
传送花开的声音
依依月意随微风
袭人 却是残香无迹
是你呵!是你
带走了梨花白的清香
——《梨花白的清香》
风起的时候
是桃花纷纷扬扬的时候
是满月儿如镜
照你低眉娇羞的时候
长发飘起来
月光,桃红色一样袭来
…………
应该祈祷
我们的世界没有下雨
只有这桃花风
踏月色而来
拂过你的脸
飘进我眼里
——《桃花风》
这些诗句意象鲜明生动、笔触细腻、情感含蓄、语言灵动,一位七尺男儿深藏于内心的千般情义,万般柔情,跃然纸上。
我们再来看看诗人的组诗《地质之恋》,其中的《血花》令人泪奔,同样是朴实的、安静的不动声色的叙述,但是无言的力量才真正令人震撼。
本来他可以不开
本来他还来得及丢车跳出
为了妻子们门前长久的盼望
为了队员们进门能听一声那羞涩的童音
为了大年三十夜大家能看看久违了的烟花
为了渐渐失控的车不掉下万丈深渊
他毅然朝山壁撞去
从此他孤零零
睡在这路边
除了组诗之外,诗人零星的几首短诗也同样令人瞩目,掩面而思。
你的飘扬
是风的语言
你的身影
是力的象征
……
在这昆仑之东
你屹立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你千年的屹立
是千年的修行
——《旗树》
是的,荒漠中的旗树是生命的奇迹,这是对荒漠中奇绝生命意志的赞美,更是对千年修行的诵扬……
我知道你走了
命运没有安排我们最后的道别
如果,你知道要走
你一定会来到我的身边
梦中的你
还是年轻的模样
我找不到你的手
我知道,你的手藏在身后
总让我牵不着
我知道,我牵你不回
你不让我去啊
——《我知道你走了》
在诗人简洁、深情、朴素而不动声色的叙述中,我听到一位知情重义的男人情真意切的倾诉,他哽咽的声音,穿透了时空,他无言的泪水,渲染着所有的记忆,拍打着所有的黄昏……
我们知道,现实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对我们处理现实经验,驾驭不同的题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诗人创作时对不同的题材就会选择不同的话语方式,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经验,而以处理宏大题旨、历史题材与现实题材而著称的诗人欧阳黔森,在处理人间烟火、柔情蜜意的题材时,依然得心应手,令人愁肠寸断,这充分彰显了诗人大驾驭与微操作兼而有之的才华,令人叫绝。
欧阳黔森诗歌创作不多,但他更加珍惜每一次心灵的盛开,每一次情感的真切涌动。原来诗人知道,追求的是源自心灵的真实情感的有效表达,不是语言的堆砌,不是故弄玄虚的晦涩,每一次创作,都是真切的思考、都是心灵的对话,都是情感的流淌,这才是诗歌最为本质的力量,这既是对诗歌的尊重,也对心灵与情感的尊重,这种超越所谓技巧的纯粹而朴实的诗意表达,才是心灵不可复制的盛开,才是情感最深刻的诠释,才是真正高级的诗歌。
那么怎样理解这些诗歌是从欧阳黔森骨头里生长出来的呢?
欧阳黔森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众所周知,60年代出生的人是崇尚英雄的一代人,是满怀敬畏之心的一代人,是最具有担当的一代人,无疑这三个方面构成一代人的重要品格。欧阳黔森自幼生活在贵州铜仁的老区,当地红色故事与苗族英雄的故事自幼滋养着他的心灵,加之早年地矿工程师的职业身份所形成的对大地的挚爱,这三个方面对欧阳黔森来说非常重要,并形成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品格,而且自始自终贯穿到其创作的方方面面,在现实生活和文学创作中就演化为一种情怀、格局、大爱、担当的场景和细节,他的众多红色题材与当下题材的小说和影视剧的横空问世,可以说都完全得益于他这个重要的人文基质与人文品格。正是由于欧阳黔森这些自幼形成的心灵情结,这种自幼对英雄的崇拜、对生于斯长于斯土地的饱含深情的挚爱,构成了其作品最坚实的人文基座,并释放出令人折服的不可替代的人文精神的光芒。
所以,当诗人面对中国地图时,他的诗绪马上在南海、在西沙、在钓鱼岛、在昆仑山上飘飞,以挚诚、饱满的情感写下组诗《那是中国神奇的版图》;在新疆采风时会写下《新疆行》;在人间烟火的记忆中写下《缘像花一样绽放》;在民族记忆中写下《白求恩》《陈纳德》《罗柏特·肖》《苏斯捷尔》;在《共和国不会忘记中》写下《江姐》《董存瑞》《刘胡兰》《雷锋》;在《地质之恋》中写下《血花》等。另外还有《旗树》《我知道你走了》《一句格言》《李彬颂》等几首短诗等诗歌,从这些诗歌篇目来看,欧阳黔森的诗歌创作脉络非常清晰而鲜明,他将“敬畏”这个词作为自己的人文基因镌刻在心灵之上,并由此在他灵魂中生长出格局、情怀、大爱、担当等人文品格。
回想起来,30年前我开始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服从心灵》,我为什么要用“服从心灵”来命名呢,就是强调诗人作家的一生,就是服从心灵的一生,完全按照自己心灵进行创作是其职业的良知,是诗人作家必须遵循的创作路径,不服从自己内心的写作都是大可怀疑的,都是不真实的写作,都是虚伪的写作,这是对文学本身的伤害与背叛,只能沦为心灵的表演者,时代的背叛者。刚刚正好在视频号上看到小说家苏童的一个视频,他说“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必须遵循自己内心的第一反应,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忠实于任何教条和任何理论,他忠实于自己的身体,真实是作家唯一的武器,”。是的,这是对文学本身的尊重,也是作家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只有在心灵真实的基础上,我们谈论作家的历史观、价值观、文学精神、美学思考才真正具有价值和意义。
四十年前,我就说过:其实艺术很简单,就是从爱出发,经过美,再到达爱,从这个意义上说,欧阳黔森的创作生涯与所取得的非凡成就体现得最为具体,最为充分,最为壮观!
妄言了这么多,我昼夜敲打的键盘似乎在提醒我不能再肆意汪洋了,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欧阳黔森的诗歌创作,我想说:欧阳黔森的诗歌完全是从体内的血汁中渗透出来,具有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的、朴素的、撼人心魄的情感的力量;他的诗歌创作是站在心灵之上的写作,是站在历史道义与人文良知上的写作,是站在人文基座上的写作,是一种具有恒久力量与诗性的写作。
2024年9月30日于贵阳南鸥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