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那些难以评说的天才们的“心理大陆”︱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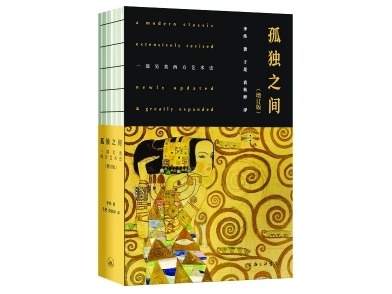 《孤独之间》 李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孤独之间》 李炜 著 上海三联书店
一位才学出众的书痴
李炜在《书城》上的艺术史随笔,有一种桀骜不驯的光彩。像一个老战士,守卫着老城堡,孤独地昂首阔步,忽而持戈起舞,忽而又灌下半缸酒来,酣畅淋漓。
他是小众读者仰望的才子,《书中书》《碎心曲》《4444》《反调》《无比的黑暗》《嫉俗》《永恒之间》等文集,横跨文学、哲学、历史、音乐、诗歌、美术等领域。对于他的长期拥趸而言,一本本读他的书就像看他展示十八般武艺——刀枪剑戟,可以!斧钺钩叉,厉害!鞭锏锤戈,不在话下!学者夏志清被他的“读书之广博通达所惊奇”,诗人余光中称他为“一位才学出众的书痴”,绝非过誉。除了闻见博洽,他的语言天分亦令人望洋兴叹——用英文写作,通晓另外七种语言,他半是调侃半是骄傲地说:“德语没好到可以去柏林的麦当劳点餐,只够用来翻译里尔克。”
虽然大学报到是在芝加哥数学系,他的心思已经飞到文学系。转系后,英文写作很是折磨了他一阵,不过,最惨痛的挫败不是在文学课上,而是在艺术史课程上。艺术史教授要求对校园中亨利·摩尔的青铜雕塑写一篇文章,李炜不知从何说起、无法交稿,只好退课。此后的大半生里,艺术史全部依赖自学,他坦白地说:“或许正是因为当年我交不出稿,如今才写了这本书。”
这本一雪前耻之作叫《孤独之间》,副标题是“一部另类西方艺术史”。
从首版的318页增加到630页
《孤独之间》的第一版出版于2017年,是李炜的第九本书。与此前的很多集子类似,他关注的依然是人,是那些肩负天才的人们在生活与历史中的沉浮遭际。如果说《反调》讲的是那些被大众忽略的天才,《嫉俗》讲的是那些与社会格格不入的天才,《孤独之间》讲的则是那些难以评论的天才:拉斐尔、乌切洛、博斯、委拉斯凯兹、修拉、席勒、德拉克罗瓦、波丘尼、马列维奇。
诗人里尔克说过:“艺术作品永远是孤独的,绝非评论可及。唯有爱能搂住它,了解它,珍惜它。”的确,很多时候,艺术作品只能欣赏、不能阐释,特别是那些冷冰冰的学术框架和分析工具,不仅不能缓解、反而会加重这种孤独。倒是出于爱的拥抱与私享,更能接近艺术本真。所以在后记里李炜不无幽默地说——
“就算我才不疏、学不浅,且有大量的纸张,我依然不会尝试去写一本货真价实的艺术史。不仅因为这样的著作不胜枚举,更是因为它们再好再厚也只能是走马看花。我更喜欢做的,是在一条路上走走停停,好好逛逛那些吸引自己、又没被大量观光客和导游破坏的景点。”
此次《孤独之间》增补版问世,从首版的318页增加到630页,在长度、厚度、深度方面都有拓展。不仅如此,他还大费周章地重译了很多章节——没错,他一贯用英文写,由译者翻译成中文,此次忍不住亲自上阵。我觉得特别的“翻译腔”是他的特色,就像童自荣配花花公子,别有声口。当一个作者不停地折腾自己和译者,他的完美主义面目自是暴露无遗。
“另类”其实是一种创新写法
“一部另类的西方艺术史”,这里的“另类”,其实是一种创新的艺术史写法。
首先,李炜不以风格流派为框架,只关注具体的艺术家们,暗合贡布里希的名言:“没有大写的艺术,只有一个个艺术家。”因为是写人,自然要有血有肉、有情有态。他擅长从艺术家们的自画像、他人为艺术家的画像入手,形神兼备。
他写丢勒,用1498年自画像:“二十六岁的丢勒面容瘦削——也可能只是因为他在威尼斯买到了一面好镜子。无论如何,他的头发变成了小卷,还蓄起了胡须,果真像他开玩笑给自己起的绰号那样,‘长发多毛的画家’。”
他写惠斯勒,以画家切斯的《惠斯勒肖像》举例,“不可或缺的‘贵公子’道具包括单片眼镜、紧身上衣、超细手杖。一头卷发和一身黑装自然也有助于形象。值得注意的还有画家的姿势以及握手杖的方式”。
当然,最深刻的分析还是直接挺进大师们的心理大陆,李炜有本事让人相信,“‘听起来’像贝多芬的德拉克洛瓦,其实一直在‘演奏’莫扎特”,也就是看起来革命,实则传统。
李炜同样明察秋毫地指出:里希特著名的灰色作品,是他个人风格的外显,或者说是没有风格的风格,“他偏爱的表达方式是轻描淡写。甚至可以说,无论在艺术界还是日常生活中,里希特都不介意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的男人’”。
其次,李炜用更符合艺术家特征的写作风格书写他们的故事,这种“实验性写作”与卓然秀出的艺术家们相得益彰、俊迈不群。“每个章节读起来都别有风趣”,需要作者苦心孤诣,也是一种另类的强迫症。例如《疯狂与理智之间》写围绕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开头用洛特雷阿蒙的金句“当缝纫机遇到雨伞”,后面的各个小节则为“当爱情遇到歇斯底里”“当手电筒遇到艺术品”“当斧头遇到颅骨”“当狮子遇到暴政”“当资本主义遇到舰艇”,一路以“达达”的方式,串联起布勒东、阿拉贡、苏波、娜迦、查拉等一长串名人,有“并置”和“自动书写”旨趣。立意之妙,恨不能为之浮一大白。
第三,李炜并不装做“客观”,他更不在行文中擦去自己的行踪,反其道而行之,他常常把“我”置于一个不容忽视的位置,或一本正经,或插科打诨。从叙事学角度,这种“元叙述”通过作者自觉暴露文本的写作过程,产生一种间离效果,还富含幽默自嘲,让人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喜剧的那种戏谑,颇能解颐。除了加强行文的趣味性,也明示了李炜对于笔下故事的绝对控制,乌切洛只是李炜笔下的乌切洛,“怪咖”全都是李炜塑造的“怪咖”。
第四,除了纵横的才情,李炜的“另类艺术史”还展示了丰沛的真知灼见。
拉斐尔一节,他有意在米开朗琪罗、达·芬奇、佩鲁吉诺和塞巴斯蒂亚诺的比较之间,铺陈拉斐尔在想法和技艺方面的“前卫”。他指出,时至今日,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受到追捧不再是因为成就非凡,而是个性独特,因此既不古怪也不抑郁的拉斐尔会被人指责“缺乏深度”。然而,拉斐尔的画作是名副其实的绝世大作,他吸取了每一种技巧,却神奇地保留了自己的风格。
惠斯勒一节,李炜总结了惠斯勒的特点:任性和“语不惊人死不休”,如果说现在他还能在艺术史上保有一席之地,“不完全是因为他确实能在画布上唤起其他艺术家无法表达的情绪,更是因为从他开始,艺术家本人——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一言一语——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说穿了,惠斯勒最优秀的作品,其实是他自己”。
全书最长的一章是写杜尚的,题为《自欺与欺人之间》,将杜尚所带动的现成品艺术、观念艺术剥皮去骨,还原到历史的大炖锅中,指出杜尚不过是个凡夫俗子,“但他无疑是这世上最幸运的艺术家。平庸至极,却照样名满天下”。在某种意义上,李炜对于正统艺术史编撰中的偏见与浅薄明察秋毫,这才使他的“另类艺术史”绝不人云亦云,相当自由,也相当睿智。
“炫学”来得举重若轻
由于李炜“一向对鲜为人知之事有强烈兴趣”,《孤独之间》充塞了大量炫学式的细节。
例如“sprezzatura”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重要词汇,或许可以译为“装腔作势”,也就是“掩饰一切技法,让所作作为表现出不费气力、浑然自成的感觉”。“谁都知道功德圆满做来不易,因此,一挥而就才会让所有人大为惊奇。反之亦然,费劲心思把一件事办好——所谓好事多磨——只会显得牵丝攀藤。”
与此类似,李炜本人的文章也有这种“sprezzatura”,事实上,他阅读了大量相关专著、书信、评论和资料,但是行文时若水银泻地,毫无滞涩之感。比如博斯一节,他显然读过大量炼金术与神秘主义的专著,但他手持奥卡姆剃刀,“一边淘汰过时的保守观点,一边去除稀奇古怪的理论”,玄奥无朋的中世纪炼金术,举重若轻地阐释完毕,只用了两千余字。
最能代表李炜水平的,当属对委拉斯凯兹《宫娥》的阐释。自从福柯写了这幅画,大家似乎只有顶礼膜拜的份,李炜却能雄辩地证明,画中主角既不是宫娥,也不是公主,甚至不是镜中的国王夫妇,画中主角恰是画家自己,他在大画布上绘制的正是我们看到的这一幅。此画是他在廷臣的屈辱中对于画家荣耀的捍卫,“难怪《宫娥》中的他会摆出如此不寻常的姿势。带着一丝冷淡,他偏立一隅。凭着一股傲气,他挺起了胸。哪怕是腓力也没他这么神气”。
(作者:马凌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
【编辑:王戎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