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中快讯|何其芳最后的长篇小说梦:《无题》
197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其芳选集》三卷本,第三卷收入何其芳的长篇小说未竞稿,小说没有题目,选集目录中直接用“无题”作为标题,选集明确标识为“长篇小说”。之所以没有标题而且是未完稿,原因是何其芳的突然离世。对于何其芳来说这是人生的一大遗憾,也是他未完成的最后的长篇小说梦想。在何其芳看来,诗歌、散文、小说、戏剧,难写的是小说和戏剧,戏剧更为难写,所以他一生除早期创作过一部《夏夜》算是戏剧作品,之后几乎未再涉及。但能创作一部有分量的小说是何其芳一直的理想。在诗歌、散文等领域,他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散文集《画梦录》更是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极其少有的大型评奖——“大公报文艺奖金”。诗歌、散文的成就更激发了何其芳小说创作的欲望,尤其是长篇小说。抗战爆发前在天津他准备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可惜只创作了四个片段,何其芳一直没有放弃长篇小说创作的梦想,直到晚年,何其芳终于动笔了一部反映知识分子走向革命道路的故事,当时何其芳身体的衰弱使他预感到自己所留下的时间已经有限,原本构想中的长篇巨著因之变得遥不可及。他深知自己对地方革命生活的直接体验匮乏,且未能搜集到足以支撑那段历史的珍贵素材,再着手撰写,无疑是力不从心之举。经过深思熟虑,何其芳作出了重大决定——转而书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正是这份对生活的深刻反思与情感的细腻捕捉,最终定格了他小说的内容,使之成为一部承载着他个人记忆与生命体悟的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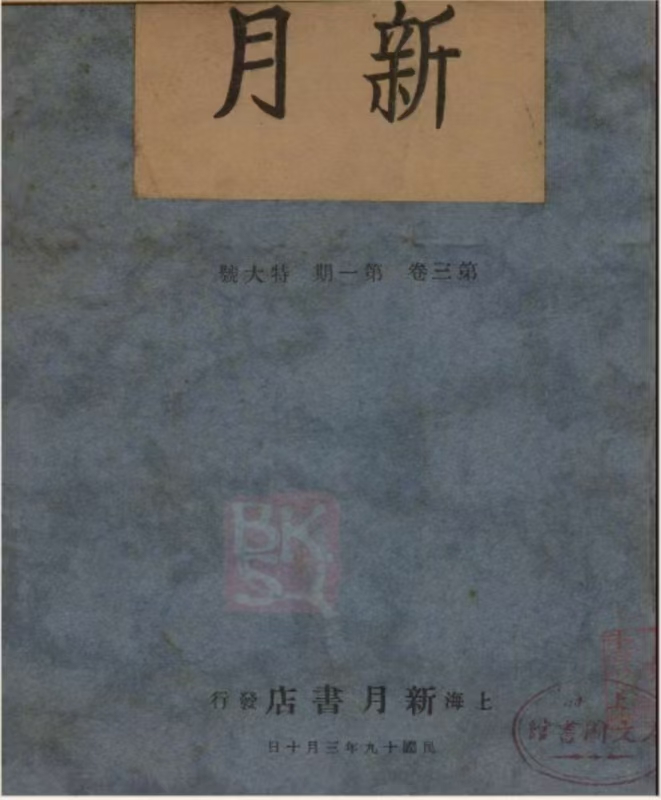
“按何其芳的初步设想,小说准备采用三部曲的形式,字数计划在100多万。第一部从童年时代写起,一直到成为青年知识分子,最后走向革命;第二部写革命经历,重点是延安生活和整风运动,写主人公思想的改造和变化;第三部写到衣村,进一步与工农兵相结合,完成灵魂的蜕变。很显然,小说的基本原型就是何其芳自己,是他以‘改造’为中心,对自己整个人生道路进行的全面总结和回顾。如果能够完成这一设想,这确是一部无论时间还是空间跨度都很宏阔的长篇巨制。”(贺仲明:《暗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页。)但遗憾的是,小说因为何其芳的匆匆离世而未完成。但也有学者提出这部未完成的书稿于何其芳的文学道路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虽然这部小说没有最后完成,但我们可以想像到,他写出来的,只能是一个政治观念的教科书, 一个改造和忏悔的历史记录。”(贺仲明:《暗哑的夜莺:何其芳评传》,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页。)
经过长期的思想淬炼,特别是在十年特殊时期的风暴之后,何其芳的文学观念遭受了深刻的转变,以至于其早年间熠熠生辉的文学才情似乎已逐渐黯淡,那份敢于探索与创新的思想勇气也隐匿难寻。加之,他并未涉足长篇小说的创作领域,积累不足,故而在晚年体力与精力均有所衰退之时,要求他自我超越,挑战未曾尝试的文学高峰,无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近乎于强人所难。如果探寻何其芳创作长篇小说的原因,他的弟弟何海若提供了一些材料,“其芳认为我们今天的社会有许许多多的人物和事件可以写,应该有许多史诗和长篇小说来表现伟大的时代变革,可是这样的作品产生得太少,与我们的时代不相称。他也说到一个文学家的成长,一部优秀的作品的产生,要具备多方面的因素。当然不是等待,而是要积极努力创造条件。”(何海若:《何其芳琐忆》,《何其芳研究资料》,四川万县师范专科学校,何其芳研究小组编1982年第1期,第6页。)可见,何其芳是带着使命感,带着对长篇小说创作的渴望创作这部作品的。这部小说没有题目,编者将其命名为《无题》,这里或许有巴金的建议成分。何其芳曾经有一种观点,据王觉回忆,记得一个炎热的夏天从印刷厂出来,太阳快要落山时,他和何其芳行走在凉风吹拂着的田野小径上。何其芳同王觉谈起他刚读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他从积极方面分析了作品主人公个人奋斗精神的社会意义,他不喜欢作品最后一部分大量讲述音乐理论,影响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人感到枯燥乏味。何其芳接着又谈起巴金的《家》在青年读者中的巨大影响,从而使他产生想用自己青年时代的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强烈愿望。他想把那些当年生活在他周围的旧制度的叛逆者,放在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中去表现他们的成长。“以后的事实证明,他在创作上的这一强烈愿望持续了许多年,为搜集这一创作素材,约在五九年左右他到过重庆一次,找了几位老人谈大革命时期四川党的斗争,并作了详细的记录。在他溘然逝世的头一年他又来过重庆一次,找到参加过北伐战争、经历过‘三·三一’惨案的周钦岳同志。据说返京以后他的这部长篇已在健康条件不能允许的情况下动笔了,但他这个酝酿多年的创作计划没有得到完成。”(何海若:《何其芳同志与1946年重庆的文学活动》,《何其芳研究资料》,四川万县师范专科学校何其芳研究小组编1982年第2期,第9页。)其实这是何其芳的遗憾,据荒煤回忆,在延安时,有一天晚上他和何其芳一起散步,谈到报告文学问题。荒煤认为,只有小说才算是真正的创作。当时的何其芳也笑了,是认同的,而且,何其芳对荒煤说:“他也不满足于写诗,认为诗究竟不能概括伟大的历史时代,他还想写长篇小说哩。”(荒煤:《忆何其芳》,《何其芳研究专集》,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但这种遗憾最终也没有补齐。
何其芳《无题》的这篇小说具有前期小说书写“青春主题”的特征,有论者就指出:“何其芳小说中的‘青春主题’则有更丰富的社会特征……这些青年形象,既展示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也呈现出何其芳以‘青年’主题来表达对个体、民族、国家出路的关怀。”(李凯:《巴蜀文艺思想史论 ——一种区域文化视阈下的考察》,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83页。)小说中写了董千里、龙于野、杜璞三个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性格气质相差很大,但共同的进步倾向,他们最终会走向革命的。作家试图通过他们在生活中的不同遭遇以及他们思想上的碰撞,证明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投身革命,他们不仅要接受斗争的血与火的考验,而且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化影响彻底决裂。在这三个人物中,杜璞出身工人家庭,思想也最为激进,他强调在工人阶级先进分子领导下的武装斗争。热衷学习革命理论,信仰共产主义,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作家是把他作为一个真正革命者来写的。龙于野是地主少爷,但由于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他不满意自己剥削阶级家庭,渴望自食其力。他说:“把家里分给我的一份土地完全还给农民”。但杜璞却指出它的空想性质:把土地还给农民,过不久就又会由地主富农吞并去了。其次,一个人这样办,对全国地主阶级剥削农民来说,什么作用也起不了。这暗示了龙于野能否最终成为革命者将是一个艰难而曲折的过程。
董千里是作家着力写的人物,是把他作为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典型刻画的。他出身书香门第,有很好的文学修养。他感谢文学、诗歌,是它们使他有了理想,有了对于人类和人类的前途的信心,而且使他不满现在这样不合理的世界。从全人物的实际表现看,文学作品对他的消极影响却是主要的,他把心肠软弱当作美德来肯定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董千里这个人物参加革命虽为必然,但却注定要经历坎坷曲折。从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的一些基本特征,尤其是自卑,打上了何其芳深深的烙印。小说开篇就写三个中学生,杜璞和龙于野同一中学,董千里在低一个年级,三人住在同一宿舍。三人相约去龙于野家中做客,在龙家做客的过程中,三人表现了很强烈的反封建和革命色彩,如对龙于野大哥龙于田女仆琼华的同情,三人与龙于野伯父家新女婿马国栋关于古文(尤其是八股文)与白话文优劣的论争,杜璞对于龙在田招待丰盛的饭菜而联想到贫苦农民。
小说还塑造了一个疯人形象,龙于野与龙于田两兄弟的父亲龙云从是一个疯子,他会写诗,而且具有反叛精神,对于囚禁他的龙于田等人包括看守张老五等人的谩骂,而且在他的诗中以及癔语中可以看出,龙云从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反而像《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表面病狂,实际清醒,而且龙云从的很多话包含着对未来的幻想,都有启蒙意义。后龙云从利用龙于野等人给予的火柴纵火逃脱,也预示着对压迫人社会环境的反抗和挣脱,富有革命意义。小说之后重点塑造了与董千里密切相关的两个家庭人物,一个是父亲董少仇,一个是董千里的姑母董少芬。父亲董少仇是一所中学的历史教员,在讲课的过程中不断加入具有思想进步意义的内容,因内容的深刻与富有启发性而深受学生爱戴,当时和国民党右派勾结起来的地方封建势力对董少仇的讲课内容进行攻击,认为他的讲课“鼓吹阶级斗争,侮辱人类尊严”,董少仇对董千里的影响很大,以致后期董千里准备去北京求学追求进步都与父亲董少仇的影响密切相关。
董千里的姑母小时候读过两年私塾,原本嫁给一个富裕之家的公子,但丈夫堕落腐化,她一气之下返回娘家,与弟弟董少仇一家生活在一起,由于董少仇早年丧妻,她负责照顾董千里,扮演了实际意义上的“母亲角色”。董千里是在姑母的呵护下长大,受姑母的影响很大。董少仇因上课思想进步而遭到学校校长的反对,准备开除董少仇,但进步学生(包括杜璞)发起学生运动,最终迫使校长改变了对董少仇的惩罚。这个情节与何其芳读书时的经历非常相似。这场风波过后,董少仇遇到了来姑母这里做客的两个女孩子叶若兰与李蜀琴,二人在成都初中毕业到北京升学,在姑母这里等几天船。在这几天里,临别前,董少仇与二人相约,以后也会去北京升学,这其实是何其芳自己的未来人生。小说到董少仇与叶若兰、李蜀琴分别结束,后续因何其芳的遗憾离世而未完成。
课题来源:202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何其芳年谱长编(1912-1977);项目编号:24BZW117
作者简介:周思辉: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