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明贤:认识脚下的土地丨屯堡书香①
编前
11月9日,屯堡文化大会将在贵州安顺召开,探讨屯堡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和核心内涵。两本新书引人注目:钱理群著《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的《屯堡▪家国六百年》。动静贵州阅读专区特邀嘉宾点评——走进屯堡,读懂贵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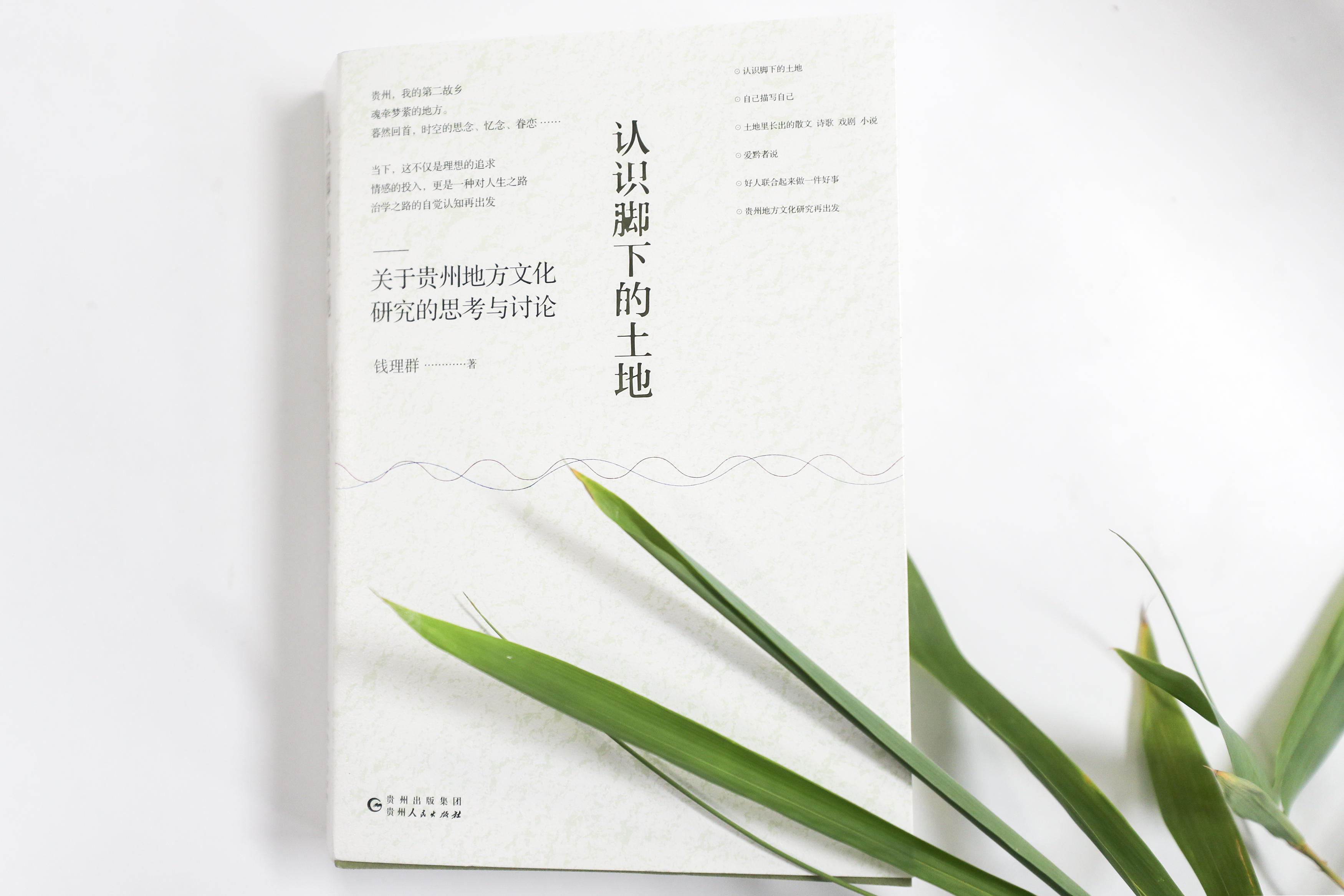
钱理群著 贵州出版集团出版 杨昌鼎 图
《认识脚下的土地》序
戴明贤
钱理群先生在我的家乡执教十八年,桃李成蹊,知交成众,粉丝成云。我却因离乡早,直到2002年,他创意并主持《贵州读本》的编撰,我受邀参与,才得识荆。但一见如故,并因此加深了一些原识乡友的情谊,结识了一些原先陌生的乡友。此后与他的交往就多起来了。他曾称他与袁本良、夏其模和我为安顺四友,四人中我年纪最长,资历却最短(而且夏先生我只慕其名而未及相识),但受益独多。
记得第一次开会议论《贵州读本》,到需要找一句诗作为全书题词时,他和我不约而同地想到艾青的两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有夸张,但能表达参与者共同的感情。那时我的系列散文《石城浮世绘》在李晓兄的督促下,正连载于《安顺晚报》;又开始酝酿写郑珍,散会后向他简单说了说这本诗传的文体设想,他很赞成,后来还在“读本”里选了一章。不久《石城浮世绘》连载完毕,发去向他请教。他是容易激动的人,一口气看完,并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杜丽女士,以极短的时间成书出版(书名易为《一个人的安顺》);又应我的请求,写了一篇很动感情的长序,从对“第二故乡”安顺的怀念之忱,引入深层的思考,强调对小地方小人物小事件的写作,于宏大叙事之正史具有不可或缺的拾遗补阙功能。我开笔写《一个人的安顺》时,完全出发于文学角度:儿时所见所闻的那些人和事,不仅熟悉,而且有趣,又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过去属于写作禁区,现在可以写了,就应该写了。后来在写作过程中,感觉它们逐渐呈现出来一种“社会生态圈”“散文体地方志”的整体性,遂据此定位,补充一些应有而尚无的内容。连载期间,编辑告诉我,报栏前的读者多了,报纸的订户增加了;有人说:这些事我也能写的呀!单行本出版后,画家陈启基写了一部《我的石阡》,贵阳刘隆民先生赠我一册《一条街上的贵阳》,都说是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这些反应当然令我欣慰,但读了理群兄的长序,基于感性的认识又得到深化,加强了自觉性,引导着此后的写作。十年后,以学者顾久兄任馆长的省文史研究馆为我组织了一次研讨会,理群兄因工作不能分身,却托孙方明兄带来一篇视野开阔、思考深刻的长文,以我的个人写作为个案,畅论贵州文化建设的大局,大大拓展了研讨的议题。
我先天拙于理性思维,后天疏于理论训练,写作多开始于一种混沌笼统的感觉;而理群兄的优长正在这些方面。我的感性写作引起他的理性思考;他的理论表达深化了我的感性写作。如果这个说法不错,也就能够解释我和理群兄为什么相识虽晚而一见如故了。
修史修志固然是我们的悠久传统,但理群兄提出并一再强调的“认识脚下的土地”的命题(以及何光渝兄“构建贵州地方文化谱系”的倡议),对安顺乃至整个贵州地方文化建设,无疑产生了很大的理论推动作用。“认识工程”已成为遍及各地的常务。他所创意并主持的《安顺城记》的修纂,这项艰巨到近乎幻想的写作工程,在顾久兄及其团队始终如一的后勤保障、众多乡友的热忱响应、杜应国兄艰苦卓绝的总纂笔耕下,历经七八寒暑,终告完成,在学术界获得应有的肯定。这是理群兄“联合几个好人做几件好事”方式的“认识工程”最大硕果。从“读本”到“城记”,二十个岁月,悄没声地把我们带进了老年。钱兄和我,更各自失去了以自己的方式默默参与“认识工程”的亲人,留下无尽的余思。那年做《贵州读本》,经验不足,文献搜索条件不够,出书后发现许多缺憾;十年后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王尧礼兄独任其难,以他致力地方文史多年的积累,做了很好的增删。今年他也届退休之年了,但劲头方兴未艾,兴趣勃勃地在为《贵州文库》这座大庙添砖加瓦。安顺方面,李择红、吴羽、孙兆霞等乡友的几个团队,继续在孜孜不倦地深入“认识脚下的这块土地”。这二十个岁月,悄没声地巩固并加深着我们这个群落的友谊亲情。
记得有一年,一个久违的名词“乡愁”突然走红。当然是作广义的使用。又不约而同地引起理群兄和我的思考。广义的乡愁,我觉得是一种隔了时间和空间的深沉的思念、忆念、眷念。它是《诗经·蒹葭》中的那个“伊人”,一个不停地吸引和召唤你上天入地去寻找和追随的存在。我时不时会无端回忆起一个已远去半个多世纪的场景:一个晴好的午间,我坐在一幢瓦屋的后园里看书,面对一小块家庭蔬菜地,玉米和甜秆高粱比人还高,大叶片绿沉沉的。轻而软的和风,把村女的笑闹声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掠过大块大块的稻田,清晰地送进我耳朵。空气太透明,我竟能分辨出房东的女儿明慧和她的几个伴的声音,她们在龙骨水车上比赛“打飞车”。瓦匠师傅的小孙子狗儿轻脚轻手地从屋里出来,钻进园子,折了一根甜秆,又轻手轻脚走去(他怕姐姐黄敏分他的甜秆)……这是农村撑过三年困难、开始恢复元气时,我参加一个写作组,在黔北一个叫三岔河的村子住了几个月的一个午后。那天我脚气发作,没有参加田间劳动……这也是乡愁吧。我更喜欢“精神家园”这个词:心灵的安身立命之所。可以是血肉相连,也可以是邂逅,却是一样的牵心挂肠。我想,正是这种无端的牵挂和追踪,驱使我成为文学的爱好者和写作者;驱使理群兄执着地提醒人们认识脚下的土地;驱使本良兄为故乡外省异国他邦的土地写下美好的诗篇;让我们不期而然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我与理群先生各方面的差距很大,虽忝为知交,对他的著作只能拜读学习,不能置喙雌黄。因此他为我写过许多文字,我却愧不能报。这次嘱我写这篇序言,虽明白他以此作为友谊的体现,仍有惶惶之感。好在此书专收与贵州有关的文字,有的事我参与过,大部分已读过,十分亲切,就记述一些前尘琐事以报命吧。前几年我骨折躺在医院里,本良时常用微信传来新诗,我勉为其难凑些俚句奉和。当时正好理群伉俪回到安顺小住,本良告诉我一个有趣的小故事:理群先生的一位粉丝专诚从南方飞京造访,纵谈今日学界只见学术不涉思想。通宵达旦,直至电梯握别,仍立谈不舍。我想象场面,联思其人,不禁莞尔,诌了一首打油诗,在他到医院看我时献给他:
闻客来天外,千里访钱子。举目皆学术,思想付白纸。剧谈继日夜,握别兴未止。似续新世说,神气正如此。笑颜若弥勒,卓识似增矢。思虑驰八极,手足不逾咫。举箸忘辨味,脑波正电驶。览胜引冥想,花鸟无暇齿。对客话如瀑,胜解陈甘旨。书斋执鼠标,四壁默如死。著述倍等身,黄钟传角徵。大心化锋刃,毫末辨朱紫。好者如醍酬,恶之成怨皆。甘为孺子牛,冷对千夫指。君为国士材,予乃淮北枳。赖以习安缘,友伦及尘滓。
记得那天崔老师兴致很高,唱了好几首只有我和她还能知道的很老很老的老歌。
2024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