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历史笔记 | 多元与共生并存的贵州耕读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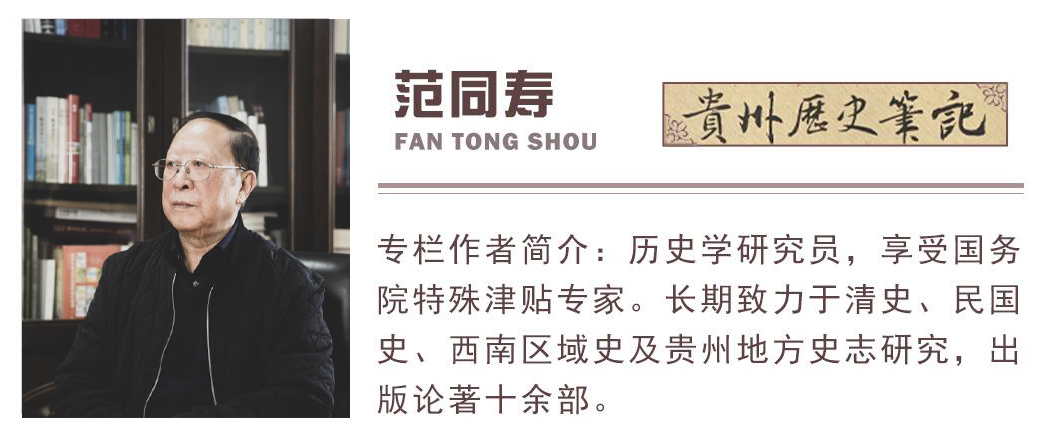

中华民族的耕读文化源远流长,其发端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那时虽有“君子谋道不谋食”的孔子和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孟子等儒学大家,同时也出现了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讽刺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荷蓧”丈人。当时虽无人评判两者的对错,但到南北朝以后,《颜氏家训》提出“要当穑而食,桑麻而衣”。张履祥在《训子语》里说“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这种冲破儒家传统观念的现象,显示的正是古代耕读文化的诞生。
农业耕作由史前社会的采集发展而来,是人类历史上由攫取经济到生产经济的伟大革命性转变,具有划时代意义。我国最早记述农耕的是《诗经·豳风·七月》,其中的“八月剥枣,十月获稻”说明那时稻作已在农耕中出现。其后,关于农业与耕作的著作越来越多,达300余部。早期以北魏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内容最为丰富。到了明末,曾任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成为一部荟萃感性认知、结合理论认知的菁华之作。

贵州特殊的区位、地形地貌、社会发展轨迹,使这片山地高原成为中国古代耕读文化的沃土。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许多民族都是稻作民族,具体到某一民族开始从事稻作的时间,却无准确的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那就是封建时代的贵州稻作文化,与各民族迁入贵州前的文化传统有着不可切割的联系。
21世纪初,考古学者对位于威宁县境内属商周时代的鸡公山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在两次发掘的出土物中,获得炭化植物种子上万粒,其中包括稻谷、粟、黍和芸薹属植物四个种类,稻谷和芸薹属植物种子数量占到了出土植物种子的99%。尽管一些学者因这些植物种子中掺杂有经过蒸煮后稻米团状炭化遗存,而认为“占大多数的稻谷和芸薹属植物很可能就是祭祀活动的遗物。”这反而说明稻作在当地的出现,时间上可能较商周时期还早。

在贵州少数民族中有着许多关于种稻的传说。一位学者在《农业考古》上发表的文章,列举了苗族关于稻种起源的传说。文章称:开天劈地之初,发生了大洪水,洪水冲掉了人们还没来得及收割的稻谷,幸而老鼠家族贡献出了储存的稻子,人们才恢复了稻子的种植。另一则传说是一只狗受人们的委托向天神要来五尺穗、五尺茎秆的水稻,使先民得以开始种植水稻。传说虽未必可信,但若剔除其中的神话色彩,则可以从中窥视出苗族与稻谷种植的密切关系,以及种植这种作物的大体时间。
布依族是我国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之一。一位名谷因的学者在《布依族稻作文化及其起源》中认为,壮侗语族在未分化之前,他们共同的祖先创造了稻作农耕,并举出以汉语记录保存下来的布依民间古籍《请谷魂》中的相关内容为证。《请谷魂》属布依族的原始宗教经文,约300余行,“作品首先解说稻子歉收的原因,说稻谷有灵魂,稻子生长不好,是因为谷魂走了,被洪水冲走,被蚂蚁搬进窝,被雀鸟衔上山崖,被水牛践踏入土,被亡人带回祖先故地……”于是要“请管人间的老祖母‘印孔婆’和创稻作的老祖母‘浪阿婆’送谷魂回来”。由此可见,布依族从事稻作至少应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1999年出版的《布依族文化研究》则进一步具体指出:“从战国时代到西汉末年,分布在北盘江流域的布依族先民,是夜郎国的主要居民之一”,随着汉族大姓势力的崛起,“布依族地区的封建领主经济已完全确立,大部分地区已从‘刀耕火种’‘赶山吃饭’的原始耕作方式进入了犁耕稻作阶段”。
或许由于贵州多数世居民族属于稻作民族,加之西汉以降内地的生产、生活方式大量传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通过各种渠道在僻处西南的贵州高原传播开来。于是,除了山高险阻、相对封闭的边远地区,耕与读的结合便在汉族移民相对较多的地区,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贵州虽僻处西南,耕读文化的出现并不比其他地区晚,这种文化不仅影响贵州自身,在一定时期、一定的社会背景下,甚至曾对中国耕读文化乃至社会进程,都曾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
古代贵州耕读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亮点。
两汉时期是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阶段,东汉时的尹珍是其代表人物。此外,曾任“犍为郡文学卒史”的舍人,著有《尔雅注》三卷,这是“汉儒释经之始”。这一学术成就既是贵州古代辉煌文化的一页,也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师从司马相如的盛览,返乡后授徒开启地方文教之门。这几位先贤,都是古代贵州“耕读文化”的奠基者。
魏晋至宋元是耕读文化在贵州高原枝繁叶茂的时期。南中之战后,诸葛亮在今贵州地区发展生产,传授百工技艺等先进的生产技术,举秀才贤良以补人才之不足;唐代充州(今黔东北一带)人赵国珍因功获授黔州观察使,后擢升为工部尚书;南宋末年的冉琎、冉璞兄弟,营造出改变中国数十年政治格局的合川钓鱼城等,皆是范例。
明清之际贵州耕读文化的特点是蔚然成风。随着数以十万计汉族军士、家属、行商、坐贾的到来,中华民族大一统的理念逐渐深入贵州山区,即便最边远的县乡也有家国理念的传播。从明初开始,教育在贵州不仅得到重视,而且发展迅速。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本身文化程度不高,却很看重人才的作用,大呼:“贤才,国之宝也”“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教化”。在“足衣食者在于劝农,明教化者在于兴学校”思想的推动下,洪武年间贵州首先办起了宣慰使司儒学,选派了学官。其后,各地相继兴教设学,除各府、州、县学外,土司统治地区的司学、驻军所在地的卫学亦先后创建,颇显遍地开花之势。

作为行省的贵州,自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才获准开设乡试,但却出现了知识分子的群体崛起的局面。据《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作者蓝勇)一书载:有明一代,云南人口占西南地区的30%左右,进士人数却只占4.5%,当时的贵州人口占约占西南地区的7%,进士人数却达到了总人口的4.5%,足见贵州教育发展之快。不仅如此,明清之际,贵州还涌现出许多名臣、名家。这些人的成功以及他们的活动,对耕读文化在各地区、各民族中的普及,以及提升贵州在全国的形象方面,都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长期被边缘化了的黔省,由此逐渐进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
清代贵州的学校教育发展十分迅速。在推行崇儒兴学、政教并举的同时,府州县学、书院之外,又增设了社学和义学。官学私塾并行发展是清代贵州教育的一大特点,不唯城镇私塾林立,即便僻远村寨也办起了各类私塾教授民族子弟。有关文献记载,到了清末,仅紫云一县的私塾这多达250余所。而在全省私塾中,最负盛名的首数遵义禹门的黎氏家塾。黎氏自迁入贵州以来,重视教育、倡导文化,注重人才培养,讲求耕读传家。“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与这一教育方式与黎氏家风有着密切的关联。
清末名臣黎庶昌所撰的《遵义沙滩黎氏家谱》,堪称明清贵州耕读文化的一种缩影。《黎氏家谱》中的《长山公手书国士祖行实》记载:“治家有道,内外必肃以耕读、勤俭、孝友。垂训后人,饮食衣服,一缕一粟必爱惜之。遇喜筵、寿节、岁时,毋靡费、毋奢华” “每岁麦熟时,以麦杆多编草帽,遍赐族人,为蔽日具耕者、纺织者。 必教之早夜勤谨,毋惰田功,毋旷机抒”。这活脱脱是一幅耕读传家画卷,其地位堪与《颜氏家训》比肩。

贵州耕读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多元与共生并存。贵州是中国古代南方四大族系迁徙的交汇地,耕读文化也表现出多元的特点。在独特地形地貌的制约下,尽管随着汉族文化的传播,传统儒家思想逐渐扩散,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日益深化,但这并不妨碍各民族保持自身的文化要素。相反,各民族在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的同时,继续世代传承着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并创造出适应本民族、本地区的独特耕读文化传统。这种多元耕读文化的保存与共生,呈现出海纳百川的胸襟,对来自发达地区的移民更有益,对自身社会进步与各民族对先进文化的吸取更有益。我们在在探讨历史上贵州的耕读文化时,不可不对此加以关注。
文化与文明是有着不同义域的两个概念。现代文明是对历史文化的革新与再造,封建时代的耕读文化,反映的是那个绵延几千年的时代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征途中,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无疑需要继承和弘扬,然而,更应以发展社会学的视角,去关注历史上耕读文化向当代耕读文明升华后,对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对于贵州来说,从古代耕读文化到当代耕读文明的演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种质的提升。我们既需要看到今天的耕读文明与古代耕读文化的内在联系(即文化传承关系),也要看到21世纪贵州的耕读文明,经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和创新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变化。
耕读文明可以更好地展示贵州山地文化的内涵和特征,展现当代贵州耕读文化的风采。如果我们深入地考察当代贵州耕读文明,不难发现,今天的耕读文明,不仅有许多古代耕读文化所不具备的、升华到了全新高度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在许多领域实现了与时代的有机结合。
深入了解贵州古代耕读文化与现代耕读文明,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贵州更好地完成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意识到这一点,才能深刻感觉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也才能感觉到历史上的贵州传统耕读文化,以及在21世纪所能持续发挥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