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可说丨登山千寻梯,下阪九仞井,明代状元杨慎的“罗甸曲”歌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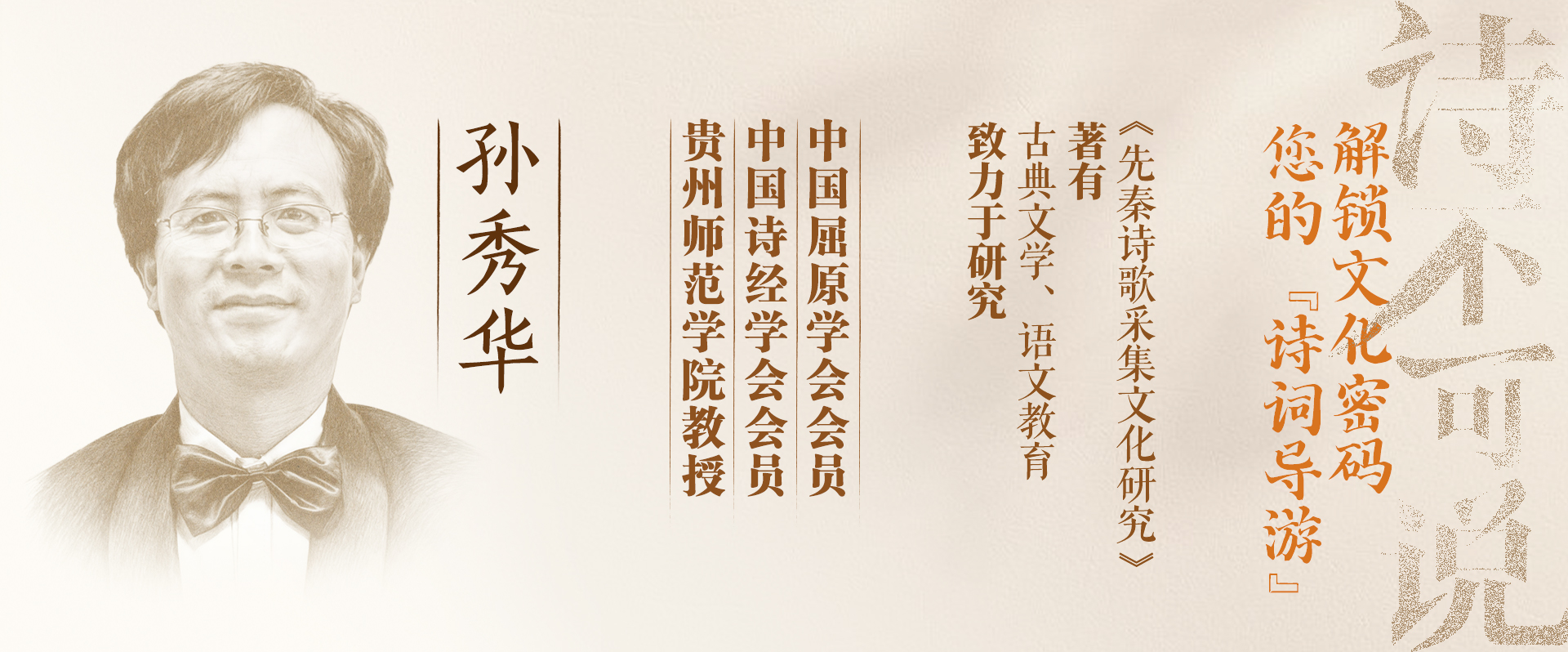
杨慎是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殿试状元,因“大礼议”事件被世宗皇帝贬谪至云南永昌卫,流放生涯长达三十余年。杨慎的老家在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杨慎遭贬谪后又在探视父病、回乡葬父、寄寓江阳(今四川泸州)等机缘下,多次穿行贵州,写下了贵州行旅诗词作品十余首,其中有著名的组诗《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
杨慎《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诗曰:
其一
百里驰驱倦,三更梦魂归。
不辞昼夜苦,但使逢春晖。
其二
山围罗甸国,水绕的澄桥。
桥下东流水,可惜无兰桡。
其三
寒灯閟孤馆,阴云锁重城。
长夜恒思晓,久雨恒思晴。
其四
登山千寻梯,下阪九仞井。
雨润衣珠融,风吹鬓毛冷。
其五
蛮树不凋叶,蛮云不放晴。
长亭望不见,何处是渣城。
其六
林间山胡鸟,声声啼我前。
何似故园里,花亭闻杜鹃。
明代时所称的“罗甸”与当今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的罗甸县并不相同。杨慎诗中有“罗甸国”之说,所指区域为主要涵盖今毕节一带,而其诗词所点出的地名确也有涉及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所辖县,据此可确知杨慎从四川到云南所途经的便是这“罗甸”至云南的“官道”。明代“罗甸”到云南的驿道属于湘黔滇驿道体系,起点是罗甸国(今毕节一带),沿驿道布防大量卫所,如云山屯(位于今贵州安顺西秀区七眼桥镇)等地的递运所、急递铺等设施,至横山寨(今广西百色田东县平马镇),再延伸至云南,是连接罗甸国至云南的重要交通干线,主要功能包括军事防御、物资运输和行政管理等。

“乌蒙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水滩……”杨慎《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组诗“其二”有“山围罗甸国,水绕的澄桥”之语,这“的澄桥”,即可确信为今毕节市黔西市杜鹃街道西门河上的“滴澄桥”。
 黔西市杜鹃街道西门河上的“滴澄桥” 图源:黔西融媒
黔西市杜鹃街道西门河上的“滴澄桥” 图源:黔西融媒
“的澄”的字面意思是说桥下河水“的的确确澄净清澈”,含有赞美之意。至于该桥名何时、如何从“的澄”讹传误传为“滴澄”,则不可知。
但无论如何,滴澄桥是一座三孔石拱桥,始建于600多年前,是奢香夫人主持修建的水西驿古驿道遗迹之一,是龙场九驿的重要节点,连接中原文化与水西地区,见证了彝汉文化交融。滴澄桥现存拱券结构,栏柱部分残损,但整体上看仍属保存完好。站立滴澄桥头,看那桥下流水潺潺,不舍昼夜,也让人不由悬想,当年过桥远行的状元杨慎,是如何心生希冀,盼望“桥下东流水”能够流水载舟,顺流而下,方可以回到自己思念的故乡。
杨慎《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组诗“其四”歌云:“登山千寻梯,下阪九仞井。”山高、路陡,下到谷底,若处深井,艰险重重,让人浩叹。组诗“其五”有曰:“蛮树不凋叶,蛮云不放晴。”贵州山野间常绿植物众多,经冬仍郁郁青青,这也让长期生活于京师北京的杨慎感叹不已。而更让这位长期在北方生活的状元感到不适的则是贵州“天无三日晴”的阴雨绵绵天气,因此才有“蛮云不放晴”之说。回溯到《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组诗“其三”,杨慎写“阴云锁重城”,又说“久雨恒思晴”;“其四”则有云:“雨润衣珠融,风吹鬓毛冷。”

杨慎还有一首五言绝句写罗甸山雨之愁、跋涉客途之悲,则更为直抒胸臆。杨慎《风雨》诗云:
罗甸愁山雨,滇阳怯海风。
可怜风雨夜,长在客途中。

对于他者杨慎而言,“罗甸”是异域,其笔下的贵州,首先是一个地理学意义上的边缘空间,与他的贬谪之地云南在心理感受上是完全一致的。贬谪之初,途经贵州,杨慎所记载的首先是苦不堪言。
杨慎《恩遣戍滇纪行》有曰:
鬼方昔云遐,罗甸今初入。
阴霾暄凝交,瘴岚昏晓集。
长亭此驿遥,只尺如棘涩。
石行蹶昆蹄,沙炊咽蒸粒。
断肠盘江河,销魂宠嵷坡。
军堡鸣笳近,蛮营荷戟多。
三辰晦光彩,七旬历滂沱。
罽衣行风舞,芦笙眺月歌。
可怜异方乐,令人玄鬒皤。
杨慎《恩遣戍滇纪行》长达1200字,这是选自其中关于贵州“纪行”的段落。诗句里杨慎夸张地说他所感受到的是“阴霾”与“瘴岚”,以及“断肠”与“销魂”。
杨慎《踏莎行·贵州尾洒驿元夕》词云:
罗甸林中,新盘山下。村灯社鼓元宵夜。东风卷地瘴云开,月明满野寒星挂。
白雪歌声,青钱酒价。当年乐事凭谁话。寂寥孤馆坐愁人,小窗横影梅枝亚。

在贵州过元宵节,人在旅途,孤独寂寞冷,愁绪满怀抱,杨慎不由不自认“寂寥孤馆坐愁人”。而杨慎过元宵节的那个“贵州尾洒驿”,极有可能位于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辖晴隆县县城。
“尾洒”系苗语,为“水下”之意。尾洒驿始设于元代,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置尾洒驿紧卫,继在今晴隆县城内设尾洒堡。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由指挥使梁海择地,在尾洒堡设安南卫,建安南卫城,隶属安平守巡道,为滇黔驿道重要节点。
但杨慎《踏莎行·贵州尾洒驿元夕》词还提到了另一个重要的地名,说是这贵州尾洒驿位于“新盘山下”。而“新盘山”或即今“棋盘山”,棋盘山现仍有古驿道留存。如此综合考察,则杨慎笔下的“贵州尾洒驿”应处于今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贞丰县小屯镇尾洒村。该村现今仍名“尾洒”,古有“维藩城”之称,是杨慎词中所称的“贵州尾洒驿”的可能性更大。古“维藩城”呈椭方形,置东、南、西、北城门四洞。东门外棋盘山有驿道,下接石桥,分别贯通花江、龙场。现存西、南面城垣一段及城东门外水井、驿道、石桥。驿道长1200余米,宽1.2米,青石铺墁。
杨慎还有一首《罗甸吟》诗曰:
苴兰方号鬼,贵竹甸名罗。
牛涔枉称海,骏坂犹题坡。
林余楚筚辂,杙识汉牂牁。
久戍劳行恻,天高奈若何。
“天高”暗示山高,预示着“天高路远”,杨慎只是在徒唤“奈何”吗?当然不是,杨慎并不满足于单纯记录旅途的艰辛,而是将这种艰辛转化为一种审美体验,这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空间重构——通过诗意的凝视,将原本作为流放之路的险阻山水,重塑为能够寄托情感与思想的美学空间。
再进一层,虽然贵州是异乡,但杨慎悉心感悟,还是总能在他乡移情到故乡。杨慎《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其六》歌曰:
林间山胡鸟,声声啼我前。
何似故园里,花亭闻杜鹃。
这首诗显然化用了“杜鹃啼血”的典故以表达深切的故园之思,但杨慎将其置于贵州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写贵州的山鸟鸣叫声声,通过这种方式,他将一个原本陌生的地理空间,纳入了熟悉的文学传统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其异质性。这种做法,不仅是一种诗歌技巧,可能更是一种文化策略——通过将陌生空间纳入熟悉的符号系统,缓解了流放者面对异质文化时的不安与焦虑。
明代状元杨慎的“罗甸曲”歌唱,以《罗甸曲·贵州道中六首》为中心解读,将“罗甸”的奇异风光与人文风貌引入诗美视野,自然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行旅诗范畴,而成为一部记录流放者通过地理空间书写而重构精神家园的心灵史诗。今天,当我们重读杨慎的这些贵州诗词,可以感受到他那在逆境中不断寻求超越的心灵的跳动,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杨慎的贵州行,既是被迫的流放苦旅,也是自主的精神探险,最终通往那更广阔的心灵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