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千年侗歌,年轻人身上传承和保护中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侗族大歌这样的评价:“一个民族的声音,一种人类的文化”。

1986年侗族大歌
登上了法国巴黎金秋艺术节的舞台
第一次亮相
便技惊四座
法国的多家媒体热烈地报道了这次演出
自此
侗族大歌墙内开花墙外香
被认为是“清泉般闪光的音乐
掠过古梦边缘的旋律”

潘迎香,在贵州财经大学,毕业照
潘迎香,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村侗族姑娘,2017年毕业于从江一中,曾就读贵州财经大学,正在备考上海音乐学院,目前是一名文艺工作者。这一期小编与大家分享这位潘姑娘和侗族大歌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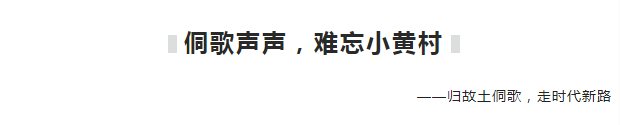
一、去听听历史怎么说
缓缓穿寨而过的小溪上跨着六座风雨桥,青山环抱的寨中耸立着四座鼓楼,几百栋吊脚木楼依山傍水而建,古井、古墓石刻诉说着这里悠久的历史。这里,便是小黄村,一个位于贵州省从江县城东北面的侗族聚居村落,在2014年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侗寨 航拍图
潘迎香就出生在小黄村,“迎香”是1997年出生时长辈为她取的名字——为迎接香港回归。在大山深处,名字往往寄托着人们最朴素的愿望,比如家与国的安康。
据说侗族大歌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现在已经有 2500 多年的历史,它没有文字,通过口传亲授的方式传给下一代。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明代邝露的《赤雅》中“侗人善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关于侗族大歌的起源,民间流传着这样这一个传说:以前侗寨里非常安静,突然有一天,一个叫九龙塘的地方变得非常热闹,显得侗寨很冷清。原来是一个叫四艾的年轻人组织他们的歌队去九龙潭里面寻歌。八九个人组成一个歌队,大家随身挑着扁担去寻歌,只有那位叫四爱的年轻人坚持到了最后并找到了歌的种子。他就用随身拿的扁担把歌的种子带回了侗寨,歌的种子太重导致扁担裂成了两块,有一半的歌的种子被河水冲走了,歌的种子在冲走的时候,住在河道两边的人捡到了部分歌的种子,所以都说侗族人是居住在河道两边的。
多声部的侗族大歌的出现打破了西方人的陈旧观念——中国民歌是单旋律的,没有复调音乐。与西方合唱团上台前需要出标准音不同,在侗族村寨男女老少随时都能唱,开口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个音高,唱出纯人声的天籁之美。山歌从山谷里诞生,踩着溪水的节拍和土地的韵律,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带上大山的原始印迹。回归血脉里泥土的律动,方觉歌声清耳悦心。
在小黄村,人人会唱歌,处处有歌,事事用歌。天天晚上唱歌,是侗族“饭养身、歌养心”最具体的体现。在侗乡,歌声在触碰耳膜的一瞬,心与世界便是共通的——田野、月亮、云朵、晚霞、青山、小狗、稻香……在大自然中长大的侗寨儿女,个个能歌善舞。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侗寨
侗族群众在鼓楼唱侗歌
潘迎香说,侗寨的夜晚是这样的——鼓楼里生着火和漫天星光相辉映,劳作了一天的侗族儿女们满含着内心温婉的情感,化作一曲曲大歌,在鼓楼的中心绕梁,而后散发在侗乡的夜空里。在音乐盛宴中,也有来自大自然的协助:响震山林、呼唤神灵的芦笙,熊熊燃烧、涅槃重生的篝火,那绵延不断的歌也都是千百年前的侗族祖先从大自然中获得启发创作流传下来的古歌,那闪闪发亮、叮当作响的侗族盛装也是侗族祖先与大自然合作传承下来的手作技艺。
贵州省从江县高增乡小黄侗寨 侗族群众在鼓楼对歌
在“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的生活方式里,蕴藏着无限智慧。侗家人无比爱恋这片土地,侗歌让那些为生活忙碌、为生计漂泊的年轻人,不忘祖先的历史,让年迈的老人能因存留前辈的记忆而有一份生存的尊严。它作为一种共同的记忆,连接着祖先和后辈,整合着村落与社会。成年后、离家后、失意后,去唱歌,在一来一回的婉转中,久违的乡情纷至沓来,浓浓的亲情如期而至,曾经的仇怨涣然冰释,童年的情谊再袭心头。岁月流转,时光匆匆,发达的科技代替了很多东西,也代替不了一些东西。正如她说的,就像会写诗的机器人无法代替河马和普希金一样,侗歌也不会被代替。侗寨儿女唱天、唱地、唱父母、唱爱情,一生悲喜唱天地万物,侗歌保护着万千情感,没有比这更让人魂牵梦萦的了。
在侗寨,把日子放在歌里,灵魂就有了选择。所有的不满、愤懑、忧伤,所有的陶然、惊喜、感动,所有的渴盼、思考、阅历,都在歌里跃动。从庸碌的日常里抽出身来,在田野中高歌,听到山谷那边传来回声,对侗寨儿女来说,就像中了奖,有种不足为外人道的快乐和惊喜。

全民唱歌,是一场盛大的集体共修。侗寨里的小孩刚会说话后,就开口学唱歌了,妈妈陪着坐在鼓楼的凳子上唱歌。如果小孩唱错了,坐在后面的妈妈就会帮小孩唱。等到四五岁的时候,小朋友就要正式加入村里集体性的歌唱活动,女生直至出嫁前都是如此,他们一生都在歌里过。侗寨就像一张网,网的核心是侗歌,将所有人捕捉在一起。集体歌唱,全民参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专属的歌队,孩子、青少年,老人等等,大家逢年过节都要聚在一起唱歌。小孩长大外出工作,也会建群云聊天、云唱歌。唱着唱着,那些堵塞的情感,流通了;那些隐藏的情绪,被看见了;那些执着的东西,放下了。所有的一切:沉甸甸的收获,得不到的痛苦,身心的紧张疲惫,找不到方向的迷茫,成功的幸福和喜悦,一切开心的不开心的,都在歌声中被看见、被清理、被放下,就像落叶回归泥土成为营养,身心轻盈了,能量充足了,就有新的力量迎接生活和挑战。
潘迎香说“回家就是充电,电满了,就要出发了”。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侗乡孩子特有的淳朴,被美育滋养出的真、善、美,夺目得让人移不开眼,让人无比渴望了解她的过去。
二、爱唱侗歌的女孩走出去了
在小黄村,刚出生下来的小孩就已经被编入同龄歌队,三、四岁时正式进入歌堂学歌。潘迎香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自小就在小黄村听着侗族大歌长大,所以她对音乐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那是对家乡民族文化的自信和热爱。这种自信和热爱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上大学前,她前前后后已经参加了不少节目录制和大型比赛活动,并在活动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学六年级的迎香就去北京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得到了时任国家主席的胡锦涛爷爷的接见。同时还参加过很多文化交流活动,比如上海世博会,陕西民族文化交流会等。
随着民族文化的重视,侗族大歌的影响力也很大。高中在从江一中就读,她认识了杨静美老师和梁进远老师,两位老师都非常专业,对学生要求严格但很友好。

潘迎香在高中时期参加校园歌唱比赛
2017年对于潘迎香来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高考年。和大多数学子一样,她努力备战,专心复习。艺考选曲时,需要结合自身条件选定歌曲,有一定的难度,杨老师一直给予她指导与帮助,陪着她打磨曲子、加紧训练。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一年,她通过艺考,以优异的成绩被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音乐学专业录取,师从贵州省侗族音乐专家吴培安老师,从此走上传承侗族文化的道路。回忆过去,她表示自己很幸运。侗歌让她见到了许多外面的世界,遇见恩师,走进了大学校园,成长为一个发光的青年人。

潘迎香在大学期间参加演出活动。左3
潘迎香说,整个侗寨的村民文化程度不高,但是他们的歌艺和手艺都特别好,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可以通过唱家乡的歌考入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很多人都认为,乡村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但在她眼里,小黄村代表着美好与希望。她说,如果年轻的一代能把本民族的文化与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带着侗族文化走出去,对文化传承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她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侗族大歌、了解侗族大歌、爱上侗族大歌。感激杨老师和梁老师为传承侗族文化与培养侗寨儿女所做出的努力,她也从未忘记自己多年来受到的美育教育的熏陶,时刻谨记自己从小黄村出发的初心——把外面的知识带回侗乡。美的教育在她身上是那么深入,让人无法忽视她眼中的熠熠星光。
三、做美的传播者
侗族大歌是侗家人精神世界里的一蔬一饭,高兴时唱、悲伤时唱、日常唱,节庆也唱。在歌里,有歌师的坚守,有杨、梁两位师者的教诲,有无数侗寨儿女的传承,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我们知道,比起物质上的短缺,精神上的失落和孤独是更难消解的,幸运的是,小黄村的人们并没有这样的烦恼。

潘迎香在小黄侗寨做调研活动。左2
潘迎香大学本科毕业之后,投入到侗歌的保护与记录中。在调研的过程中,她了解到很多的歌师,他们一生坎坷,其中有很多歌师都是一边独自把小孩拉扯长大,一边坚持传承和保护侗族大歌。他们去鼓楼唱歌都是无偿的,完全凭借热爱。歌师们愿意在他们很不容易的生活中,挤出时间来,投入歌里去。潘迎香谈到,一位歌师的经历令她印象特别深刻。她离异带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一度沦落到去城里捡垃圾,但尽管如此艰苦,她还是每天晚上坚持唱歌到天亮,以排解自身的忧愁。这是发自内心的一种热爱,是这样的文化和艺术给了歌师生活下去的希望,也是侗歌给侗寨儿女的精神上的熏陶和滋养。

潘迎香参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首批优秀成果推介会。左1
潘迎香在2018年受邀参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首批优秀成果推介会时,看到了很多非遗传承人。其中侗族琵琶的传承人吴家兴老师的事迹深深地打动了她,她为这样纯粹的赤子之心所动容。她说,唱歌二十多年,那是第一次在台上有过不专业的行为,吴老师的那首侗族琵琶歌《丢久不见长相思》,她是流着泪唱完的。
从那次去参加了推介会后,潘迎香就慢慢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因为侗族大歌是口传心授的,没有通过文字记录像书本那样把它传承下来,她想改变这样的现状。科技发展到如今,包括她在内的许多侗族儿女都想借助科技与影视的力量去把它传承和保护下来,这是记忆也是记录、是传唱也是传承。他们想让侗家人的历史、文化与传统在美妙的歌声里绵延不绝。他们在尝试录歌、录视频、做成乐谱,用汉字谐音代替侗语,做成一本书,据说书上会有现场视频的二维码,即扫即听。

潘迎香在使用相机记录侗族大歌
过去一年,她把主要的精力投入到了学习中,不过在其他方面也没有停下脚步,仍一直参与到侗族文化的宣传工作中。谈到未来的规划,她想往音乐影像志学这个方向发展,谈及缘由,她说“想通过学习专业知识抢救侗族非遗”,言语朴素,字字真切。身上的责任让她越来越有动力,朋友圈里每天都是侗乡与侗歌的影子,年前直播带货将黔东南的特产宣传出去,年后参加各种各样的大型演出,整个人自信又活泼。

潘迎香在北京参加中国东盟日活动。后排左4
她说,小时候大家都喜欢唱侗歌,长大后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迫于生活的压力选择从事与家乡文化并不相关的职业。但在他们的内心中,是有一颗种子的,他们也想让种子发芽,可是很多时候力不从心。相比于外面不远千里来到侗乡挖掘、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学者,侗寨儿女少了一些文化自信与自觉。对于这一点,潘迎香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她认为文化是我们未来造血的血细胞组织,自己要全力保护和弘扬它们。脚踏故土,伴着侗歌赶路,我们看到,侗寨儿女身上有着一种独属于艺术与自然的美感,像歌声一样,缓和、美妙、从容。
通过侗歌,我们窥见了侗寨儿女的生活状态——可爱、自由、美好。真正使人沉迷的是那种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它来自于古老歌声的美丽和神秘——歌声里有鸟语、蝉鸣、犬吠,日升月落、鸟鸣虫吟都在歌声里错落有致,自然纯粹,万物生长。侗族大歌为儿女们提供了一种身处五湖四海却同呼吸、共命运的实感,让他们真正实现了在一起。这种相互支撑、相互温暖的力量,或许就是民族文化的本质。一个人牵挂另一个人,一群人眷恋一个村落,一个村落再影响更多的地方。这样的联结,虽然很微弱,很渺小,但它就像种子,萌发,生长,从每一个侗寨儿女开始,让他们从物质或精神上变得更富足,帮助她们更有勇气和力量地面对他人,面对世界,从一个忙碌、拘束的身份中蜕变出来,奔向自由广袤的天地。

侗歌响起的一刻,美,震撼人心,我不再是我,我和你成为了“我们”。
我有幸在美中成长,
也将致力于把美传给你,
让这歌声穿过漆黑的夜空,
穿过重掩的树林,
穿过这片哺育万千生命的土地,
在天地间疾呼美育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