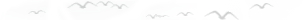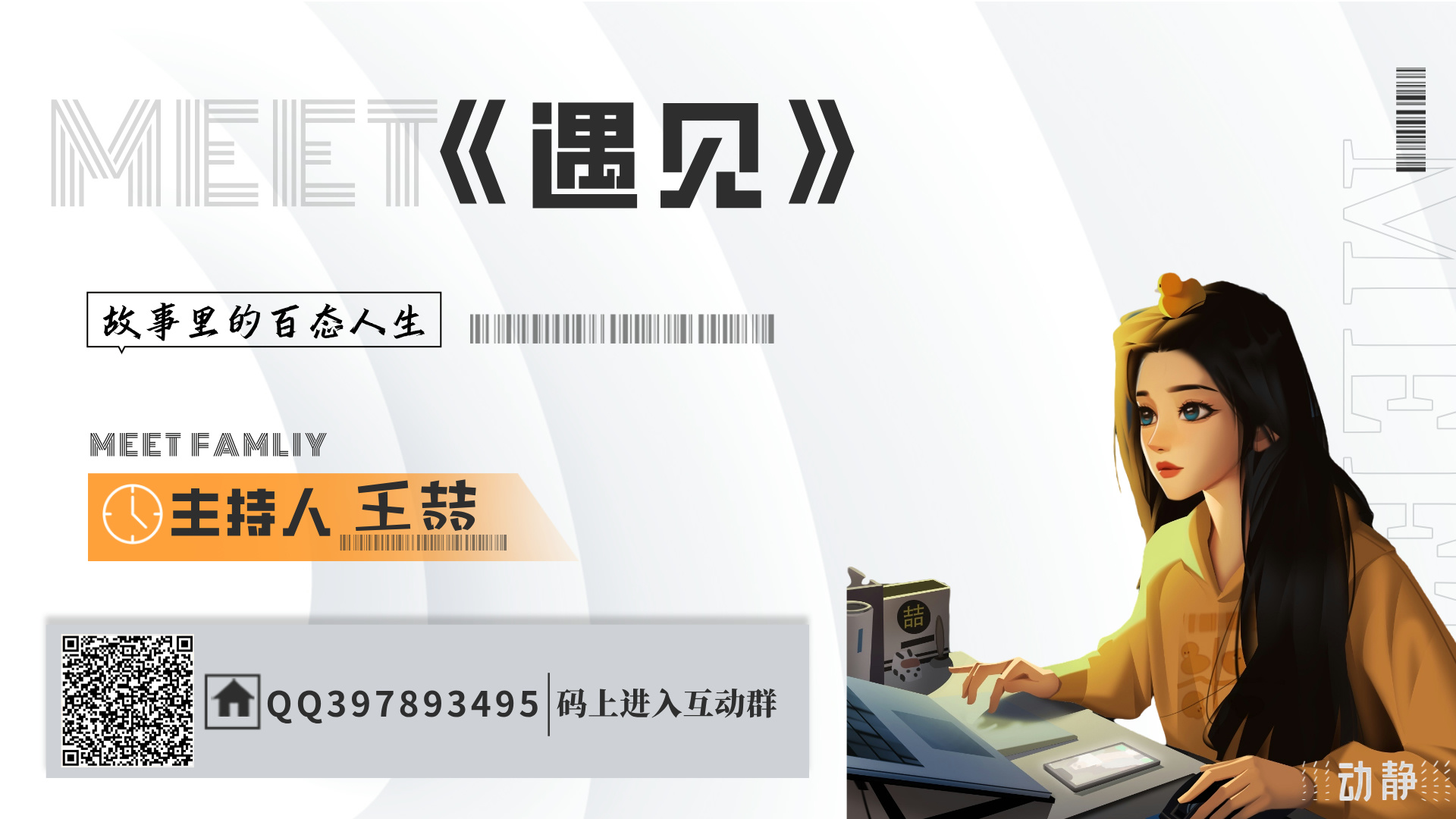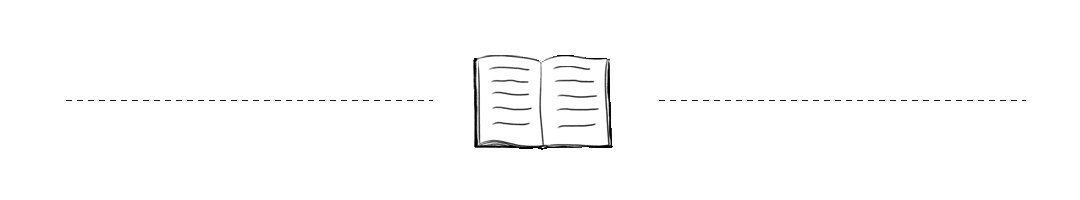遇见|话筒与镜头间,与自己重逢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害怕被人讨厌?经常会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胡思乱想了很久?人活一世,没有人能活成一座孤岛,总是需要与人打交道。但遇到的人越多,就越容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陷入极度的自我内耗,不是永远在讨好别人,就是在做不敢拒绝别人的事。如果你也曾经陷入,或者正在经历这样的内耗,不妨试着读一读《被讨厌的勇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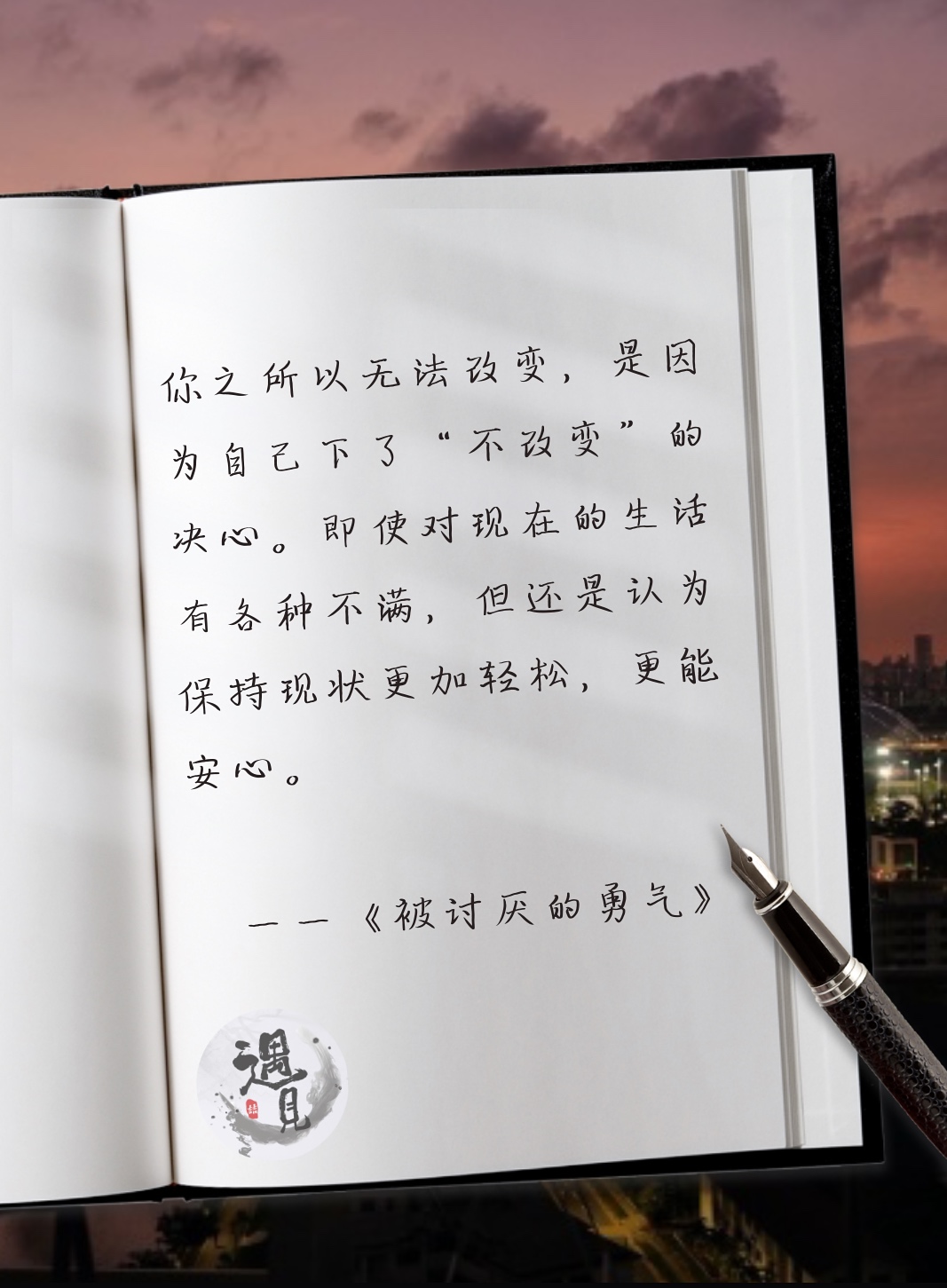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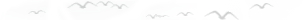
深夜,台灯在稿纸上晕开暖黄色涟漪,电脑屏幕突然亮起,一封邮件轻轻叩响深夜的寂静:“主持人,这些年我总在失眠的夜里反复咀嚼别人的评价——同事的冷言、父母的期待、甚至陌生人的眼光……直到昨夜,我竟睡了七小时。因为我想通了,别人的看法,本就不该是我人生的闹钟。”
这让我想起好友小林的故事。她曾是办公室里最“拼”的姑娘,每天最早到岗最晚离开,团建时永远负责活跃气氛,朋友圈的点赞也要算着时间挨个回应。可这样的她,却在某个凌晨发来消息:“喆,你知道吗?我数了三千只羊,却数不清自己为什么活得这么累。”


文字在视网膜上泛起涟漪,恍惚间看见2013年某个凌晨的导播间。指尖无意识摩挲着老麦克风磨砂质感的防喷罩,这只小小的麦克风,承载了我五千多个日日夜夜的倾诉,它就像一个忠实的伙伴,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如今,它静静地躺在电台空置的直播间深处,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
记得初入行时,师傅教我的“四勤”准则就像刻在骨子里——腿勤、嘴勤、脑勤、笔勤。那时的直播间像精密仪器车间,要同时盯着主播台、备播电脑、CD机、话筒线路,还得抽空看时间、对稿件、读导播手势。同事笑说我们不是主播,是八爪鱼。而我深知,在这个岗位上,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否则一失万无。上厕所卡着广告间隙,呼吸声都要拿捏分寸。


可正是这样的日子,把我打磨成现在的模样。有一次粉丝问我:“主持人是不是不能随时出去玩?”我打趣道:“云游算不算?早上直播下午剪辑,晚上写稿审核,家人朋友打开节目就能知道我在哪。”这句玩笑背后,藏着多少深夜独自回家的身影。那些被路灯拉长的影子,就像成长路上无声的见证者。
时光匆匆,媒体融合时代的浪潮汹涌而来,全媒体传播矩阵成为主流媒体的标配。我们顺应时代的发展,转型投入短视频的汪洋大海。看着三年前抖音上最后更新的那条生活随拍视频,望着20万粉丝的留言区,那些老粉丝的询问“啥时候复播?”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我回复道:“在学用眼睛给你们说晚安呢,即将归来!”就像小林最新发布的朋友圈里那张穿着晚礼服主持的照片配文:“蝴蝶振翅从不为证明什么,春天自会循声而来。”我们都在努力挣脱那些束缚自己的枷锁,寻找属于自己的春天。


改变,始于那个暴雨滂沱的夜晚。导播盯着监视器,突然笑着说:“你刚刚分享故事的时候我的镜头在抖!”我的心猛地一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接着说:“像蝴蝶停在麦穗上,有种老电台的治愈感。”那一刻,控制台的蓝光里,十四年的夜风与崭新的光影悄然相拥。原来转型不是告别,而是与更好的自己重逢。
在大家的帮助下,我像蹒跚学步的孩童重新认识镜头。一期期的上镜直播节目实践中,我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拍摄搭档第三次喊停,我不再焦虑别人的眼光,而是凑近监视器认真分析:“空镜接特写会不会断层?加个推镜过渡呢?”就像小林终于看懂评审表上的专业批注,我也在分镜脚本的批注海里,打捞起镜头语言的珍珠。


真正破茧是在临时接到解说乒乓球赛的那次。当镜头中的王楚钦反手拧拉的瞬间,我脱口喊出“漂亮”,手心的汗珠与观众席的呐喊同时蒸腾。搭档摘下耳机那句“挺棒的”,恍如当年听众在午夜发来的“晚安”。收工后,我望着高架桥上的车河,川流不息的车辆就像人生的轨迹,各自奔赴着不同的方向。忽然明白,镜头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话筒,介质终会改变,但心底的热爱永不褪色。
走过广电大楼的玻璃幕墙,我看到倒影里站着一个披头散发却目光清亮的女子……人生如舞,重要的不是抵达某个定点,而是享受每个起舞的瞬间。让我想起《被讨厌的勇气》里的话:“我们都在命运织机上穿梭,与其纠结线头的颜色,不如专注编织属于自己的图案。”你要相信,春天从不会迟到,它总在破茧的时刻悄然降临。
作者/摄影: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