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 《阳明问道》:文释阳明道,画传圣贤心
当文化自信日渐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阳明问道》的出版恰似一场及时雨。它是一把精巧的钥匙,轻轻叩开理解阳明文化的大门,让那些曾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圣贤思想,变得触手可及;更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历史与当下、思想与实践,让五百年前的智慧能直接回应当下的困惑。
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一部兼具思想深度与艺术美感的通俗读物,往往能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重要桥梁。由王修权、周建华主编,关国建绘图、谌业军撰文的《阳明问道》,作为“阳明文化通俗读物系列”的重要作品,获2024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与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双重资助。该书以阳明先生贬谪贵州龙场的生命历程为脉络,以“文”释道、以“画”映心,既系统梳理了阳明心学的诞生轨迹,又以艺术化的表达让五百年圣贤精神鲜活可触,为当代读者走近阳明文化打开了一扇兼具思想性与审美性的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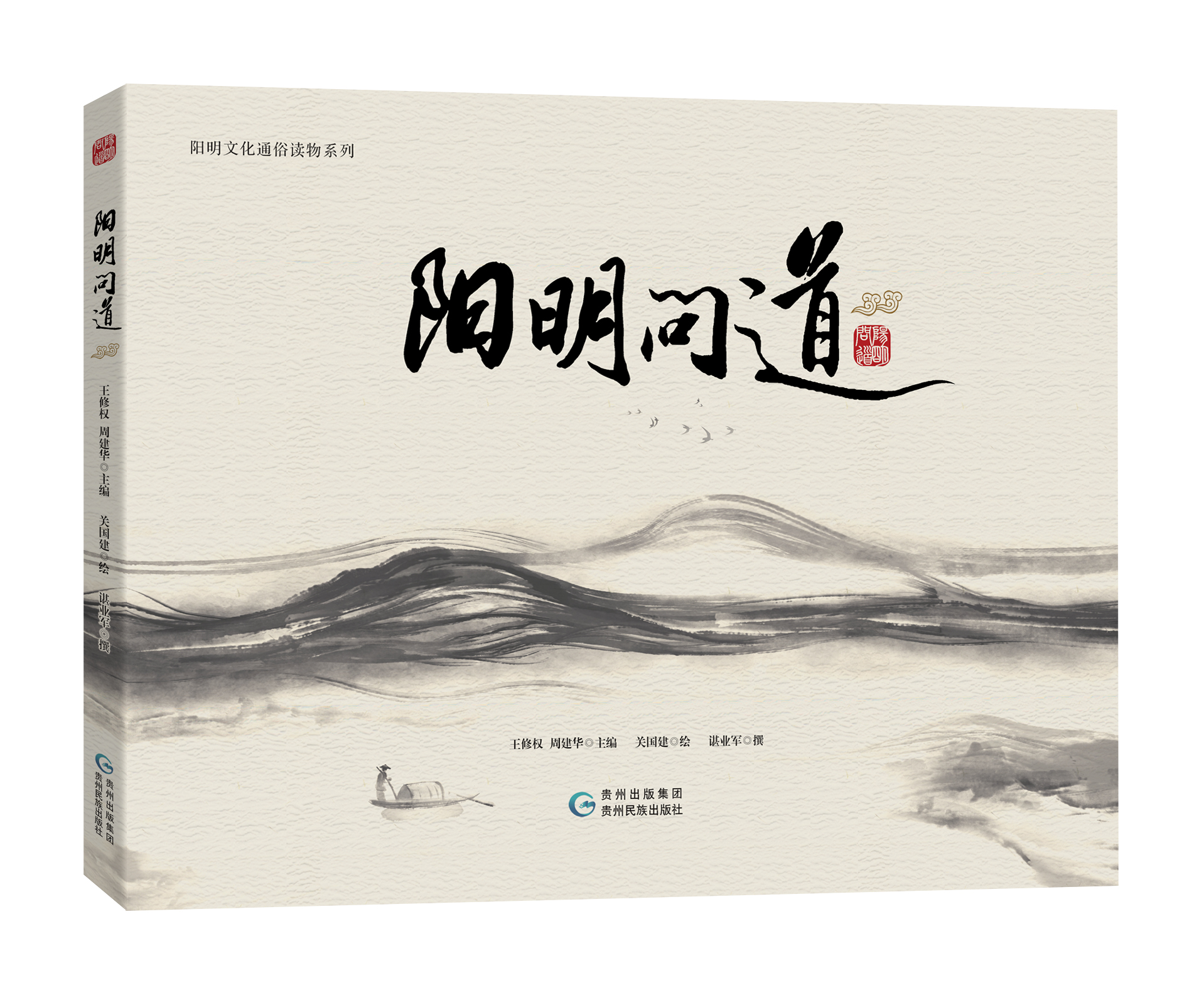
文以叙事,揭秘阳明心学的诞生脉络
《阳明问道》的文本创作,始终紧扣“问道”二字,将阳明先生的龙场岁月置于历史语境与思想演进的双重维度中展开。全书以时间为轴,从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阳明先生因上疏救友被贬龙场、次年西行入黔起笔,细致铺陈其从浙江西行,经江西过湖南入黔,并在龙场教化百姓、潜心悟道的历程。阳明先生平溪卫与王文济酬和赋诗时的顽强自信,兴隆卫书壁抒怀时的乡愁难寄,平越驿站面对七盘岭时忠孝两难的怅惘,直至甫抵龙场时面对荒芜驿站、瘴疠蛇虫的生存困境,每一段经历都以阳明先生的诗文为锚点,让那些尘封的历史场景,不再是纸页上冰冷的记载,而成为可感、可触、可共情的历史图景。
书中最具分量的笔墨,无疑凝聚于“龙场悟道”——这个中国思想史上熠熠生辉的关键节点。正德三年(1508年),阳明先生于玩易窝中枯坐研《易》,于百死千难中顿悟“格物致知”之旨,继而淬炼出“吾性自足”“知行合一”的思想精魂。这一顿悟并非空洞的哲学玄思,而是深深扎根于他结草为庵、垦荒种粟、赈济山民的现实经历,与烟火气十足的生活实践深度交融。文本通过对《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谪居粮绝请学于农将田南山咏言寄怀》等诗文的解读,展现出阳明心学“源于生活、归于心性”的特质:他向老农问稼学穑,不独为果腹之需,更是为秉持不蹉跎光阴的生命自觉;他为吏目三人挥笔作《瘗旅文》,绝非仅出于一念恻隐,更是彰显他以仁心包举宇内的儒者担当。这种将思想成长与生命实践紧密结合的叙事方式,让“知行合一”不再是悬浮的理论,而是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生准则。
此外,文本更着力挖掘阳明先生与贵州大地的深层羁绊:他应贵州宣慰使安贵荣之邀作《象祠记》,借舜以仁德感化其弟象的典故,深刻阐发“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应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之请,赴贵阳文明书院登坛讲学,让“心性之学”在黔中落地生根;他亲手营建龙冈书院、修葺何陋轩、构筑君子亭,以文化为桥,将中原礼乐文明与贵州本土风情巧妙融合,悄然影响了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书中对这些史实的细致梳理,不仅清晰还原了阳明文化在贵州的传播脉络与生根历程,更深刻揭示出传统文化因地制宜、与时俱进的蓬勃生命力,这正是当代弘扬传统文化所应秉持的核心逻辑。
画以传神,勾勒圣贤精神的视觉图景
《阳明问道》的独到之处,尤在其文画互证的巧思。关国建先生以画笔为媒,将阳明精神转化为鲜活的艺术语言。他的每一幅作品皆与诗文意境相契、与历史场景相融、与思想内核共振,最终营造出文辞有尽而画境无穷的审美意趣,让文字的留白处,尽是画笔的回甘。
画笔对历史场景的还原,既恪守细节之真,更含情感之暖。如《平溪入贵》一画:阳明先生跨一匹瘦马,斗笠斜挎肩头,正驻足远望;旁侧王文济手持木棒,俯身指点着山川风物,似在细说黔地风土;远处山驿隐在暮色里,柴门轻闭,炊烟已散。寥寥数笔间,贬谪途中的萧索与穷途仍抱青云志的自信交织,连暮色漫过山峦的厚重质感,都似可触摸。“勤力稼穑”一景更见温度:阳明先生戴笠着布衫,与仆人躬身于荒田,指尖沾泥拨土,新苗破土、绿意漫溢田间——这抹鲜活的绿意,既是垦荒劳作的生机写照,更契合“耕读传家”的儒者本真,将“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藏进了田垄间的烟火气里。《瘗旅悲情》一画则见仁心,蜈蚣坡下,阳明先生率童仆躬身祭悼吏目三人,草席覆着逝者,纸钱轻飘于风,连画中暮色都染了哀婉。风声似也低咽,将那份“民胞物与”的儒者仁心,凝在笔墨间,让“仁及苍生”的情怀不只跃于纸上,更漫进观者心底。这些画作不逐技法的华丽,只以朴素笔墨捕捉历史瞬间的情动,恰如为读者架起一座时空之桥,让人得以俯身贴近阳明先生的精神世界。
更难得的是,绘画对阳明思想的可视化转译,多以虚实相生之笔完成,让抽象哲思有了可感的形态。《玩易窝悟道》一画堪称典范:洞穴内油灯已残,灯芯余温似散未散,石桌上纸墨静卧,墨迹尚润;而端坐的阳明先生周身仿佛有微光萦绕,身旁更隐现一头麒麟。画中实写的是悟道环境的简陋清苦,虚绘的却是“静极生慧”的思想破壁,那抹微光、那头麒麟,恰将“吾性自足”的顿悟瞬间,从抽象哲思转化为触手可及的画面。《云泉清志》则以“实景”与“幻景”交织:画面前景,阳明先生背着重药篓,与山民并肩走在山道上,草叶上的晨露仿佛仍沾附于衣角;画面后侧却淡淡晕出旧事虚影。画中一边是采药济民的入世实践,一边是远离尘嚣的出世念想,既呼应了《南溟》诗中“何时共栖息?永托云泉深”的心愿,更将出世与入世的思想抉择,藏进了虚实交织的笔墨里。
值得一提的是,画笔对贵州山水与民俗的勾勒,更让文本浸满了浓郁的黔地风情。《飞云崖奇观》中,群山绵延、小河蜿蜒、飞鸟盘旋,尽显“云贵之秀萃于斯崖”的瑰丽;《南祠咏怀》里,南霁云祠祭典上芦笙悠扬,旌旗招展,观者如云,还原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祭祀传统;《元夕制灯》一画中,童仆制灯、顽童嬉闹,简陋纸灯与京城奢华之灯形成对比,既呼应了诗文《家僮作纸灯》中“安贫乐道”的主旨,又展现了龙场百姓的生活气息。这些笔墨让阳明文化不再是孤立的思想坐标,而是深深扎根于贵州的青山绿水、民俗风情中,成为思想与地域共生的文化符号。
道以传世,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翻阅《阳明问道》,不只是回望一段尘封的历史、静心读懂一种深邃的思想,更是循着文字与画笔的脉络,去探寻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的交汇之处。阳明先生在龙场的岁月,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砺,更是于困境中悟道、于危难中传道的担当。这份逢山开路、躬身践行的坚韧品格,即便在今日,依然像一束光,照亮我们面对困境时的迷茫。
从个人修养来看,“知行合一”的理念提醒我们,道德认知需转化为实际行动,理想追求需扎根现实土壤;“吾性自足”的智慧则鼓励人们向内探求,在浮躁的社会中坚守本心、涵养心性。从社会治理来看,阳明先生以德化人的实践,为当代大国治理提供了历史借鉴;他将中原文化与贵州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做法,也为今天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递上了一份鲜活的参考。
《阳明问道》最难得的,是作为通俗读物的分寸感。它避开了学术著作的晦涩壁垒,不堆砌艰深术语,不故作高深姿态,让普通读者能轻松走进阳明先生的世界;又跳出了娱乐化解读的浅薄陷阱,不戏说历史细节,不曲解思想内核,始终对传统文化抱有敬畏之心。它以文画互证为桥梁,让文字的“理”与绘画的“情”相拥,文字讲清“悟道为何”,画笔展现“悟道如何”,让阳明文化自故纸堆中焕发生机,变得可知、可感、可学。
当文化自信日渐成为民族精神的脊梁,《阳明问道》的出版恰似一场及时雨。它是一把精巧的钥匙,轻轻叩开理解阳明文化的大门,让那些曾被视为遥不可及的圣贤思想,变得触手可及;更像一座桥梁,连接了历史与当下、思想与实践,让五百年前的智慧能直接回应当下的困惑。
愿更多读者能循着这本书的指引,走近那个在龙场草庵里“悟本心”的阳明先生,读懂“知行合一”的真谛,让圣贤精神如星火般在当代重燃,照亮更多人的心灵之路。这,或许便是《阳明问道》最珍贵的价值底色。
文:位俊达
(作者系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