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论古夜郎与古牂牁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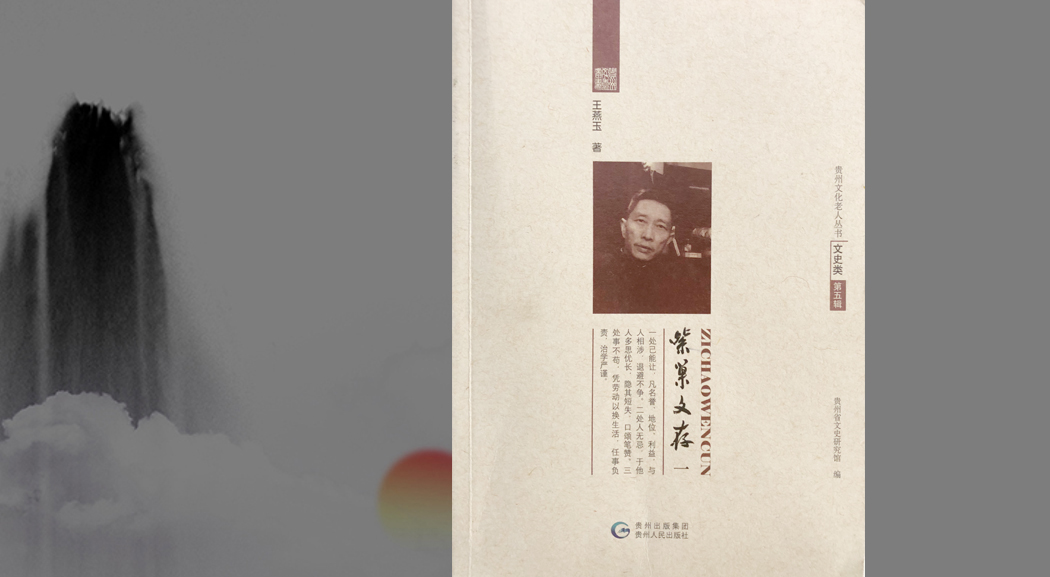
一处己能让,凡名誉、地位、利益,与人相涉,退避不争。二处人无忌,于他人多思优长,隐其短失,口颂笔赞。三处事不苟,凭劳动以换生活,任事负责,治学严谨。
——王燕玉
一
古代夜郎是贵州历史上很复杂的问题。探讨夜郎,每每牵涉到牂牁,牂牁与夜郎的关系密切相联,要弄清楚夜郎,同时必须弄清牂牁。考订最早的夜郎疆域,非考订最早的牂牁江不可。夜郎古国的缘起,可从古牂牁国找出线索,也就同时发现二者在先的渊源。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夷置牂牁郡,其主要地域是分割夜郎国的辖区设县,而又保留了一个缩小的夜郎国。晋愍帝建兴元年(公元313年)采纳南夷校尉宁州刺史王逊的规划,分牂牁郡的西南部置夜郎郡,东南部仍为牂牁郡,牂牁、夜郎东西接壤并列。南齐永明三年(公元485年)划拨牂牁郡与武陵郡间的地带置东牂牁郡,暂时未涉及夜郎。不久,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承制,以武陵与东牂牁二郡中间地侨置夜郎郡夜郎县,夜郎、牂牁又在另一形势下南北连境。历史上夜郎与牂牁的关系,起码有上述四个阶段。
古夜郎国的下限,1978年贵州史学界已经公认,是西汉成帝河平年间。牂牁太守陈立诛夜郎王兴,兴妻父翁指挟兴的儿子邪务胁众反叛,陈立率军攻灭之,夜郎国告终,这已无异议。但其上限,由于缺乏具体史料,还未明确。本文拟对此提出刍说。案古夜郎国的主要地域,为今贵州省西南部,也是古牂牁国的主要地域。在同一主要地域上,今天能见到的古代文献记载,春秋时代绝无夜郎,仅有牂牁;战国时代,可以说又没有牂牁(有一条不可靠,见后文),仅有夜郎。这就看出,古夜郎和古牂牁为承接关系,其递嬗时间在春秋、战国之交,亦即古牂牁衰竭了,古夜郎国兴起,占领了古牂牁国的主要地域,势力不断发展。从而可订古夜郎国的上限,是战国初期。这个演变所关涉的问题不少,古籍并无明显记录,前人也无完整成说,只能据少许零碎材料,细绎推论,综合出大体的轮廓。
二
牂牁国是什么情况?材料可怜得很,单单只有一条。《管子·小匡》篇记(齐)桓公曰:“余乘车之会九(近人有考证应作“六”的),兵车之会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南至吴、越、巴、牂牁、不庾、雕题、黑齿、荆夷之国,莫违寡人之命。”这条材料最先发现提出加以解说的,是清代道光年间的莫与俦,他在《都匀府南齐以上地理考》和《牂牁考》两文中,明定春秋时存在牂牁国。稍后郑珍撰《遵义府志·沿革·牂牁考》,也引据这一条,意见相同。今案《管子》这书,不是春秋管仲自著,基本上是战国时人追述管仲言行及其时史事编成,时间最近春秋,其中记载牂牁又是引用齐桓公言顺便提到,无伪造牂牁的迹象。因此,莫、郑引说,足以相信。
三
牂牁的疆域如何?当依牂牁江来划订。牂牁江的材料可分两类。一类是实际还有牂牁江的名称时直接记叙的,可叫原始材料,共有9条。《史记》《汉书》的《西南夷传》相同者4条,《汉书·武帝纪》独具者1条。《史记》最早,是现能见到记牂牁江的开始。当时,牂牁江尚为单纯的古名,既无全流的别号,又无分段的异称,并且所叙相关的事毫无矛盾,故可信赖。《汉书》的时代离古也较近,所关各条承袭《史记》,没有出入。当时水道分段异名虽已渐多,而关合起来未出现抵触,故也可信。故如今考究牂牁江,标准应当推本《史》《汉》,条文见后。《华阳国志·南中志》2条。一条说,“南越人食蒟酱,(唐)蒙问所从,曰'牂牁来’。”此条明是简化《史》《汉》词语,而使语意含混,可解为牂牁江,也可解作牂牁地方,难作确据。另一条说,“窃闻夜郎精兵可得十万,若从番禺浮船牂牁,出其不意,此制越之一奇也。”此条昧于汉初形势,妄改《史》《汉》文句生出错误,把由夜郎顺流下番禺,变为由番禺溯源上夜郎。首尾倒置,事理显然不合。《水经注·温水》一条叙:“豚水……东径牂牁且兰县,谓之牂牁水,水广数里,县临江上。”姑勿论且兰县方位,后人争议未决,至少有三点不对:一是按其语气,古牂牁水(北源东汉名豚水)似乎因汉牂牁郡得名,倒果为因;二是说水广数里,把《史》《汉》牂牁江下游在番禺的江面说成上游在牂牁郡(即古夜郎)的江面,不留意《史》《汉》还有“江广百馀步”的述说;三是讹解《史》《汉》“夜郎者临牂牁江”的语意,变为“县临江上”,不想《史》《汉》所述为夜郎国境,并非夜郎国邑即汉的夜郎县,更何况在夜郎县东边的且兰县怎么能“临”呢?唐柳宗元的两句诗可作一条,七绝《柳州寄京中亲故》第二句“牂牁水向郡前流”,七律《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第四句“牂牁南下水如汤”。这两句诗句是他谪居柳州时作,所谓“郡前”指柳州城外,所谓“南下”指从北方来。那么,牂牁水应是后来的龙江,再后改名柳江。流域倒推上去,应在战国楚黔中地即秦黔中郡即汉武陵郡内,与牂牁郡何干?大致柳氏笼统认为牂牁水在北面牂州,由北南下至柳州的水都为牂牁水所流出。这固然疏忽,不过用于文学作品,非比治史地沿革,可不必深怪,但须指出,以免引作曲据。
牂牁江的另一类材料,是实际已无牂牁江的名称时,后人考释古代牂牁江相当后代什么河流。笔者所能见到的,明、清以来,有31家7种说法。其中都江说、㵲水说、乌江说、牂江说、泗城江说、西洋江说,经过一一考校,都不能成立,惟有盘江说可取。而盘江说九家也不都对,有全错的,有正、错相杂的,有正确而欠完整具体的。大概以清《大定府志》、近人任可澄《且同亭集·牂牁江考正》、民国《贵州通志·舆地志》三家可取较多,依时序也可看出三家是逐步进展的,可惜都不周密。笔者以《史》《汉》的有关表述作准则,参合各家合理的意见推定,牂牁江应分二义。从精义说,它是专指今在望谟境内自西向东流于黔、桂界上的盘江,一名红水河,即《史》《汉》所述“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与“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语句里所指的牂牁江。古牂牁国即因最初兴起于这个流域而得名,江名在先,国名在后。从泛义说,它包括:今南盘江(汉代名桥水、温水)、北盘江(汉代名豚水、存水),南、北盘江会合于望谟境后的盘江(一名红水河);盘江流经黔、桂界上,入广西至武宣北部,会东北来之柳江后合名的黔江,黔江流至桂平东北,会西南来之郁江后合称的浔江;浔江流至梧州会北来之桂江后进入广东的西江;西江流至三水与东北来的北江、东来的东江会合,又分两流,正流过广州城南所称的番禺江,再经番禺入海。古总称牂牁江,即《史》《汉》所述“道西北牂牁江,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与“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及《汉书》叙元鼎五年,遣“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咸会番禺”语句里所指的牂牁江,因古牂牁国强盛统领这个流域面得名。全流共经滇、黔、桂、粤四省,包括今南、北盘江、盘江(即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番禺江,首尾二千馀里。
牂牁江与牂牁国,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发展过程。先有在今黔、桂界上的牂牁江(今盘江又叫红水河),某某土著族建国于这个流域,因名叫牂牁国。随后势力壮大,渐向四方开拓,西北扩至今南北盘江,接近蜀国东南境;北面扩至今乌江南岸,与北岸的鄨国分界;东北是楚国西南黔中地;东南扩至今两广大部直达南海;控制幅员相当辽阔,成为南夷著名大国。这使中原齐桓公也加以注意,吹嘘时点其名,牂牁江的名义转而跟着推广,形成上述泛义的牂牁江。在濒临精义的牂牁江北面,因是牂牁国最先发祥的所在,故为主要地域。其首邑因左近有夜山、郎山,而取名夜郎邑。强盛后向北迁移,迁移后夜郎邑的今地,仍按莫与俦、郑珍的基本考证而去其疏阔,订在今安顺市及其东南一带。
不难看出,古牂牁国从小到大是以精义的牂牁江流域为根据,顺着水道上溯下循拓占两岸地方。以当时中原大国为例,由建国至隆盛,约需百年左右,边远的邦国进展较慢,当在百年以上,故推估牂牁国上限,应始于西周中叶。其控制范围内,必是若干邑君邑长,全仗武力役属,无非听号令、纳财物,主从关系极其松散,不可理解为紧密的行政组织。
四
夜郎国怎样兴代的?在无任何史料的情况下,只能从情理上推断。早先当是古牂牁国首邑夜郎邑邻近的一个小邑,被牂牁国役使,后逐渐强大。春秋末年,牂牁国衰弱了,这个邑的君长乘机崛起,占领了牂牁国主要地域即北部,仍以夜郎邑为首邑,国号也就沿称夜郎。原牂牁国的中部南部,即泛义的牂牁江中下游,亦即今两广大部地,则为另一强大邑君占领,以番禺为首邑,那就是南越。夜郎君长不满足所占地域,向外扩张,东南征服毋敛,西南征服漏卧、鉤町,西边征服莫及同并,西北征服鳛国,夺蜀国一小片,东北攻略巴国少许地,正北征服整国,跨延江(今乌江)两岸,形成战国时期西南的大夜郎国。其东边的黔中地属楚,西边有滇国,南边即南越国,那三方都强大,看来夜郎君长不敢侵犯。
此后,文献上第一次出现夜郎,在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左右。楚遣将军庄蹻率兵溯沅水西征,夜郎邑东边的且兰邑首先被击破,夜郎君长投降。庄蹻继续西进占领滇国为王,夜郎等都受其统驭。说仔细点,是夜郎君长仅保其直辖领土,听命于滇庄蹻,原所控制的各邑君,各自分别由滇支配,大夜郎国解体。这段军事行动路线不太明确,《史记》《汉书》说是“循江”,《华阳国志》《后汉书》说是“溯沅”。近今考证家争论无定,笔者认为溯沅较合。这里可不详论,但应强调一点,庄蹻西征则为事实,仍是《史记》最早,《汉书》承袭,《华阳国志》所叙情节异于《史》《汉》,似乎别有所据,《后汉书》沿《华阳国志》。秦统一后二段时间,《史》《汉》叙“秦时常頞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华阳国志》作“秦并蜀,通五尺道,置吏主之。”置吏之意,就是设置郡县。清洪亮吉据《山海经》考秦镡成县为清开泰县(今黎平);莫与俦考秦置且兰县(今福泉),毋敛县(今独山);《贵阳府志》考秦置夜郎县(今石阡);《大定府志》考秦置汉阳县(今赫章);郑珍引《路史》据《蜀本纪》考秦置鄨县(今遵义);阎若璩考秦象郡包有今贵州南部(案即管辖镡成、毋敛、且兰、夜郎、汉阳五县)。鄨县属巴郡。这些考订有理有证,可以信取。然而,都未谈到原夜郎国怎样演变,却是莫大疏漏。
笔者推论补足,应是秦通五尺道,分割夜郎诸国部分地方设县,作以后开发的据点。夜郎诸国及滇慑于秦的威势,必然降顺臣伏,故史籍中不见任何反抗痕迹。可是不久全国动乱,西南夷地区秦所设置的郡县纷纷瓦解,恢复庄蹻王滇前的状况。故《史》《汉》叙“十馀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闭蜀故徼。”《华阳国志》叙“汉兴,遂不宾”。仍有夜郎、且兰、毋敛、漏卧、鉤町、莫、同并、鳛、鄨等国,而夜郎的势力反比从前盛强,超过西面的滇,统领上述各国,仍成为大夜郎。故《史》《汉》叙“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不受汉朝管辖,威据一方。直到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才发生变化。

王燕玉(1923-2000年),贵州遵义县人。1949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先后在遵义豫章中学、遵义第四中学、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任教。1973年调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任历史文选教研室、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81年评为副教授,1988评为教授。王燕玉先生的研究领域涉及贵州古、近代史,贵州方志及中国文学史,中国古籍文献等领域,出版了《贵州史专题考》《中国文献综说》等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专题文章。参与编撰《贵州古代史》《贵州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