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的现代风俗画——读欧阳黔森的长篇小说《莫道君行早》
读完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一些原先比较朦胧的想法变得较为清晰了,那就是自中国五四以来形成的强大的乡土文学或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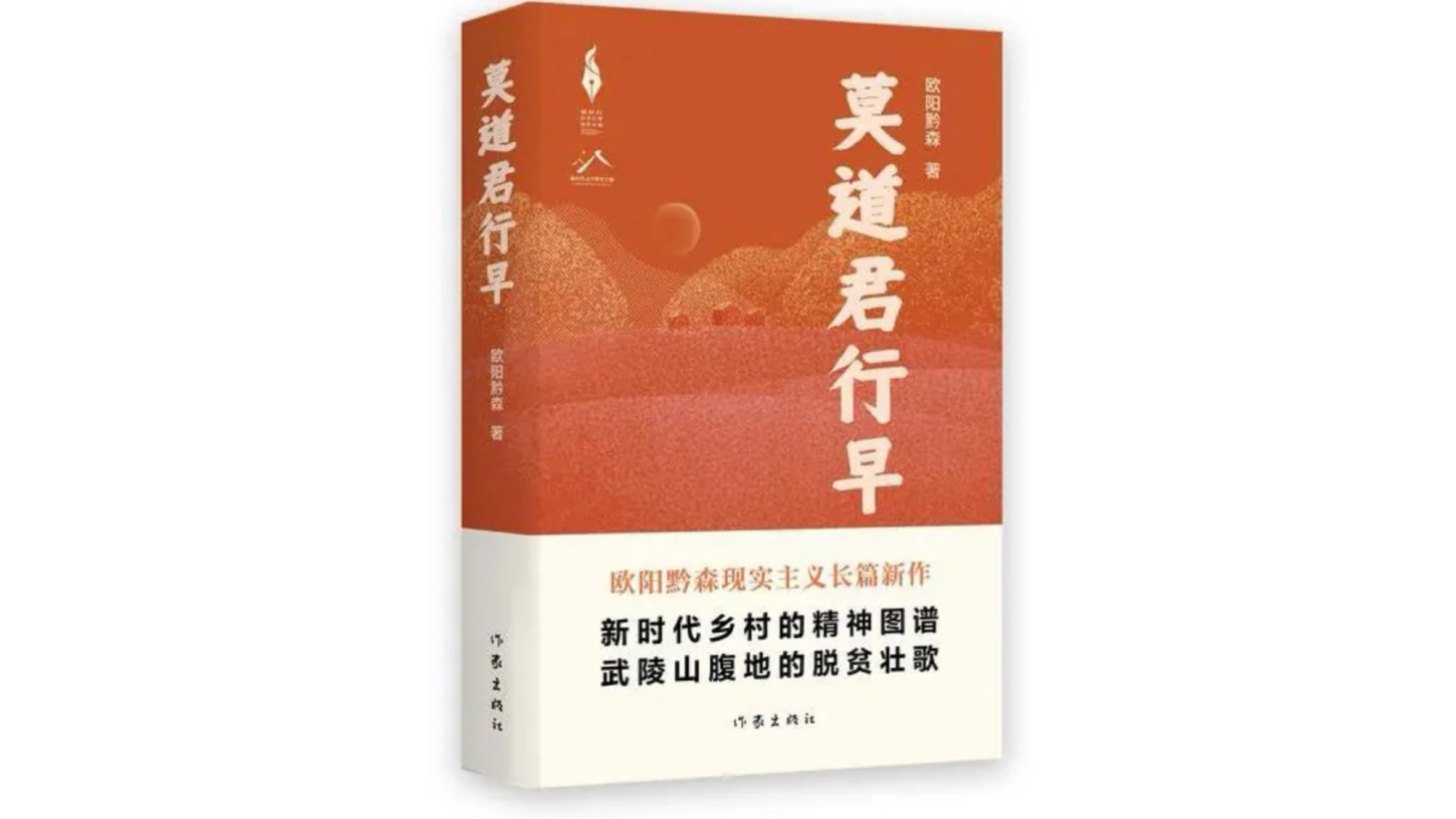
虽然,以中国悠久的农耕文明为依托,以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式叙事为结构的书写方式依然存在,但是,聚焦当下,聚焦现实的新乡土文学正越来越成为主流,并且,在纪实和非虚构文学的加持下,非虚构文学已经在建构新的叙事传统。这样的传统共时性地关注中国农村新的变革,这样传统正在努力阐释中国农村现代的社会话语、国家意志和农村新的文明形态,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比如,我们“三农”现在怎么样了?说农村空心化了,这空心是怎么个空心?城乡一体化,农村真的变成了城市吗?脱贫攻坚,成效到底如何?
新世纪以来,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到脱贫攻坚,再到现在的乡村振兴,它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又如何叙写这条不平凡的路?一方面,我们不能置复杂的传统于不顾,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在这几千年中,农村不仅为国家提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不仅为国家的延续提供绝对多的人口,而且为国家与民族创造着精神价值。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人伦道德,基于乡土基础上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一直是千百年来维系国家与社会的基本规范与情感遵循。礼失而求诸野,乡村一直是国家与民族生存的压舱石。另一方面,新农村不仅在价值建构,同时在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乃至景观形态上都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这两者的关系特别是后者已经成为当前乡土文学的叙事主体。
可以看出来,欧阳黔森的这部《莫道君行早》在这方面的美学处理更为干脆,作品的故事时间基本是与现实同步的,作品中的紫云镇是贵州武陵山区的偏僻乡村,作品重点叙说的千年村的村民们世代居住这里。但是,与同类题材的作品不同,欧阳黔森几乎没有对千年村进行历史的回溯,也没有为此塑造在传统乡土文学中经常看到的长者的形象,作家紧紧抓住脱贫攻坚的当下主题,讲述当下的故事。新农村的建设者,那些年轻的农村基层干部是作品的主要人物。
也许是欧阳黔森长期耕耘在纪实与虚构两个创作领域,因此,可以明显看出《莫道君行早》明显的非虚构风格与笔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就是在为贵州的乡村振兴作传。中国农村正在发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在进行前所未有的乡村振兴实践,这样的实践是探索性的、创新性的,前无古人,并无现成的路径与模式。而且,中国的农村由于自然、民族与文化的差异,这样的实践又有着不同的环境与路径依赖。可以说,面对传统,我们的文学可以想象,面对当下,我们的文学却无法想象,谁都不能说自己已经全知全能。因此,任何一个试图了解当代农村的人,任何一个试图以当下农村作为书写题材的人,都要踏踏实实地去了解农村,去理解农民,去认真地做一点田野调查。
在我看来,《莫道君行早》虽然是一部长篇小说,却又可以说是一个田野调查的样本。我们在这部作品中见到了中国乡村振兴的国家意志,见到了贵州武陵山区新农村建设的设计,见到了因地制宜的脱贫减贫过程,见到了目前农村的基层政治与乡村管理。作品中的千年村地处山区,土地分布零散,资源贫乏,没有一家像样的村级企业,长期在低水平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上徘徊。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让农民摆脱贫困,过上富裕美好的生活是摆在村支部和村委会面前的难题。他们首先要进行的是贵州地区新农村建设的“三改”,而要完成这一任务,第一个难题就是要对村里的居住现状进行调整,拆除影响出行与经营的住宅和违章建筑。
可以说,千年村乡村振兴的每一个工程,每一项工作都是从“破”开始的。可以想象,农民一方面向往美好的生活,但这美好的生活需要“破”,而当这“破”又是从自己开始。要改变他们目前的生活状况,比如异地搬迁时,他们又不愿意了。对于长期生活生产在农耕文明传统中的村民来说,他们习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利益,如同春种秋收一样,一切都要像田里的庄稼,他们才踏实。他们更习惯于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常常在新旧生活方式的比较中计算成本。那些美丽乡村的图景和规划是未来的,是纸上的,要让他们为了这还是当画儿看的远景牺牲眼前的利益可谓难上加难。不要说普通的村民,就是村干部都想不通,不愿做。比如村主任麻麻青蒿,村副主任罗云贵,村监委主任黄光辉等,在房屋拆迁、土地流转、迁坟等方面都疑虑重重,反反复复。
小说没有美化现实,而是写出了乡村振兴的艰辛,一些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有时,村民们的抵触可以说到了非常激烈的程度,有爬到镇政府楼上要跳楼的,有拿着菜刀闯到镇领导办公室的,有拿着农具集体拦路的……但这些困难都没有阻挡千年村振兴的步伐,相反,他们的实践生动地说明了发展中的问题只有靠发展去解决这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宝贵经验与硬道理,说明了农村的现代化的根本是农民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说明了与农村面貌变化一起的是农民的成长,农民的自我教育。
正是这些过程为作品的人物塑造提供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的典型环境,使人物形象呈现出内涵丰富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几个村干部的形象非常生动。以主要人物之一的千年村村支书兼村主任麻青蒿来说,他与下派的村第一书记肖百合不同,麻青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做过教师,有一定的文化,甚至还有过诗人的梦想,他熟悉他生于斯长于斯的村子,了解农村,了解农民,知道他们想什么,要什么,知道他们面对急剧变化的形势,面对一个又一个新的政策时复杂的心理世界。
正是对乡情、村情与民情的熟悉使他工作起来得心应手,充满了自信,并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治理资源。然而,就是这样的经验与资源又养成了他工作的惰性、武断。在他看来,千年村已经不错了,这是他多少工作的结果,他当然不愿意改变。在作品中,麻青蒿几乎没有好好说过话,动辄发脾气,他觉得千年村就是他干出来了,千年村离不开他,只有他才能做得了村支书、村主任,他是千年村的一家之主,所以总是表现出果断、甚至武断、蛮横的工作作风。为表现这一个性,小说为他安排了一个类似相声中捧哏的角色,村会计吴艾草。与麻相反,吴艾草性格懦弱,对麻青蒿唯命是从,他揣摩麻青蒿的心事,说麻青蒿想听的话,这一对比性的形象将麻青蒿的个性衬托得异常鲜明。小说真实地写出了麻青蒿这样的乡村管理者步步自封,家长式管理带来的认知上的偏差,这偏差既是对乡村建设形势与政策认识上的表面化,又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时工作上的不适应。这偏差还存在于对自我的认识上,他只知道自己是村支书、村主任,却不知道他本质上也是个农民,是与他的工作对象,他的父老乡亲面对新政策、新形势有着相同反应的农民。
当千年村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需要他率先做出牺牲时,他过不了利益关卡,迈不过情感门槛。对麻青蒿这样的人物,小说没有简单化。作品固然真实地刻画了他的不适应,他的小农思想,但是,这一人物形象的性格是双重的:他是朴素的,有着基层干部的责任与担当,有着在新农村建设中带头致富的强烈愿望,有着村级管理的智慧。小说以生动的细节、丰富的心理描写和鲜活的人物语言展示了麻的变化,并以其为中心,刻画了中国乡村基层管理者的人物群像,展现了中国农村基层的文化与政治生态。
欧阳黔森善于驾驭现实题材与宏大主题,总能从具体写作内容出发选择恰当的艺术风格。《莫道君行早》可以说举重若轻,如同轻喜剧一样,节奏明快,在幽默谐趣中呈现出具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是一次新乡土小说写作的成功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