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本良:重逢纵是秋雨天,相见却是春风面丨屯堡书香③
编前
11月9日,屯堡文化大会将在贵州安顺召开,探讨屯堡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和核心内涵。两本新书引人注目:钱理群著《认识脚下的土地》和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与中国国家地理地道风物联合出品的《屯堡▪家国六百年》。动静贵州阅读专区特邀嘉宾导读——走进屯堡,读懂贵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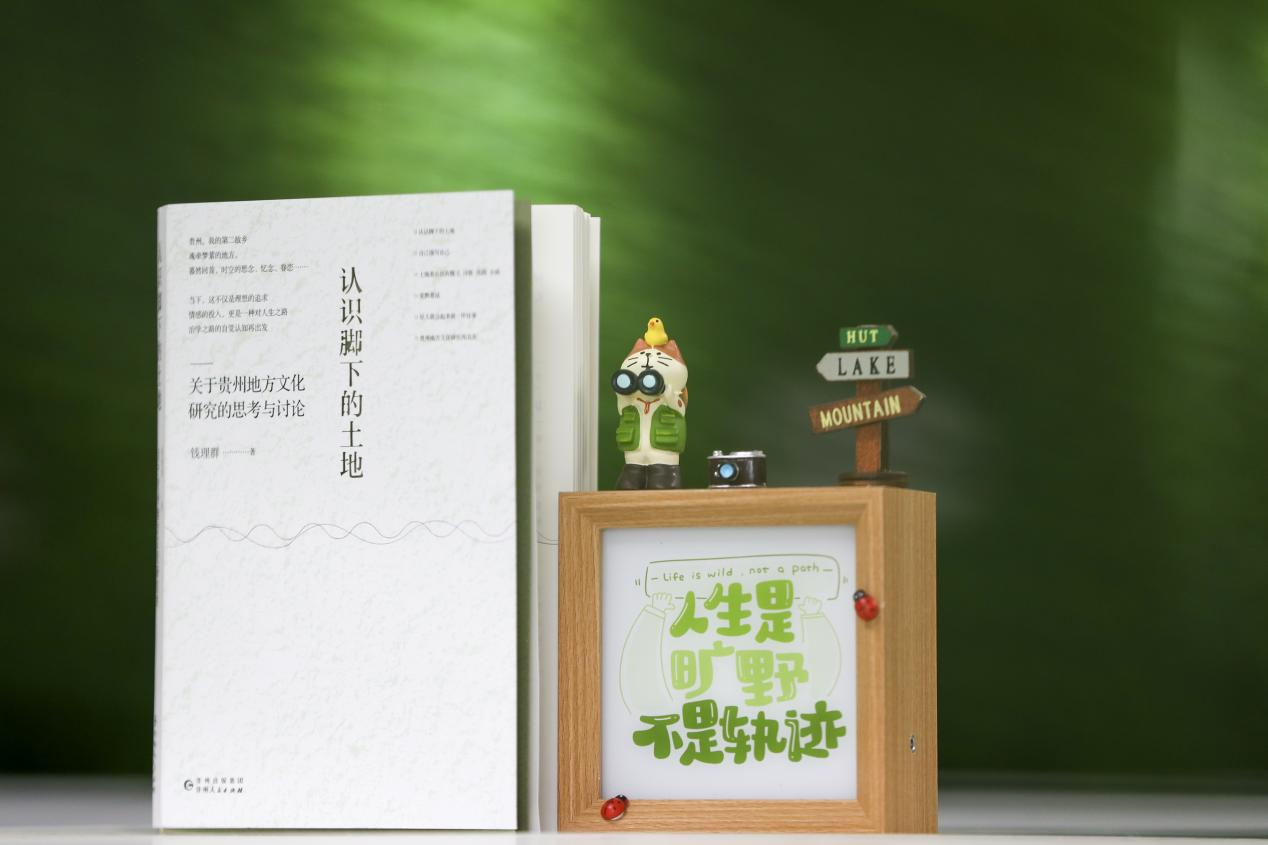
钱理群著 《认识脚下的土地》贵州出版集团出版
杨昌鼎图
脚下的土地 心中的至情
袁本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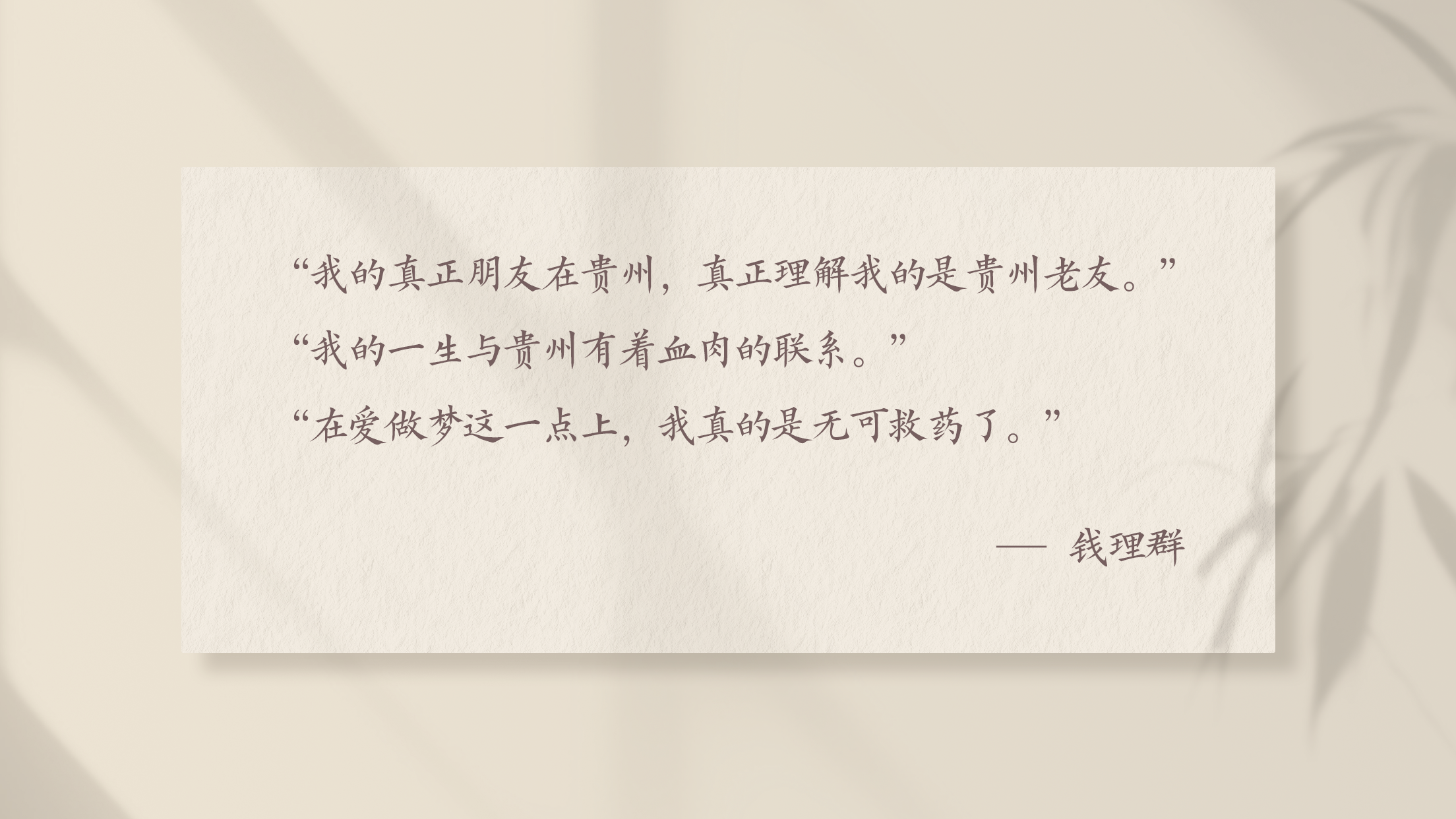
今年六七月间,理群兄从北京回到贵州小住。我先后在安顺和花溪与他相处了四天,这真是多年来难得的机会。在我俩一起工作过的娄家坡(现为安顺学院校址,以前是安顺师范学校),故地相逢,追思往事,心绪难抑,我因此有《沁园春》词一首寄慨。
疫后倖存,垂暮相期,故地重逢。正季当仲夏,节临端午;风生畅爽,雨幻涳蒙。花影参差,水光湛淡,楼宇青山绿树中。茗烟袅,且开襟促膝,聊慰离悰。回眸岁月匆匆。娄湖岸,杳茫昔日踪。忆陋房几栋,昏灯数盏;尘氛多扰,冥思无穷。晚步三人,素怀一路,怅憾而今遗两翁。至情在,是兹生大幸,馀尽鸡虫。
——《沁园春·娄家坡晤老钱兼怀老夏》
蓦然回首,我与理群兄相识相交已逾半个世纪。1972年,我们俩先后进入安顺师范学校,成为同一个教研组的同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特殊时期,社会环境纷纭混乱,学校没有正常的教学活动,只忙于“斗批改”、开门办学、支农劳动。作为教师,面对无书可教而且随时可能接受批判的情况,思想上自然有不少的迷惑和压抑。我和老钱,还有我们语文组最年长的夏其模先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成为可以倾心交谈的朋友。夏老师是1931年生人,比我大十五岁;理群兄是1939年生,大我七岁。因为共同的忧时感事的情怀、不愿随波逐流的品性、对于平静正常生活的企望,还有对于文学专业的爱好,使我们走到了一起。学校旁娄家坡水库岸边的漫步闲谈,一度成为我们三人晚饭后的共同功课。老夏对于世事人情的透辟见解,老钱对于人生理想的不懈追寻,都让刚工作不久的我十分折服,对我后来的为人为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78年,老钱考上北大研究生离开了安顺;1996年,老夏不幸病故,永远离开了我们;同年我也调到贵阳,离开了工作二十余年的娄家坡。老友星散,南北暌违,阴阳隔阻;时光荏苒,故地变迁,旧迹难觅。但我们都十分珍视那一段难忘岁月的记忆。理群曾在他的文章中慨叹“如今‘三人行’中少一人”;拙词中的“晚步三人,素怀一路,怅憾而今遗两翁”,也正是对于昔年旧谊的追怀和纪念。
理群兄是一个十分重情念旧的人。他对安顺的老朋友,对他曾经生活过十八年的安顺和贵州,从来是一往情深。他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我的真正朋友在贵州,真正理解我的是贵州老友”,“真正的知音、知己在安顺”;“我的一生与贵州有着血肉的联系”,“我生命的底子是在贵州奠定的”,“贵州是我的精神栖息”,“回到贵州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读他的著作和文章,这些带着深挚情感的话总是让我们这些贵州乡友心动和感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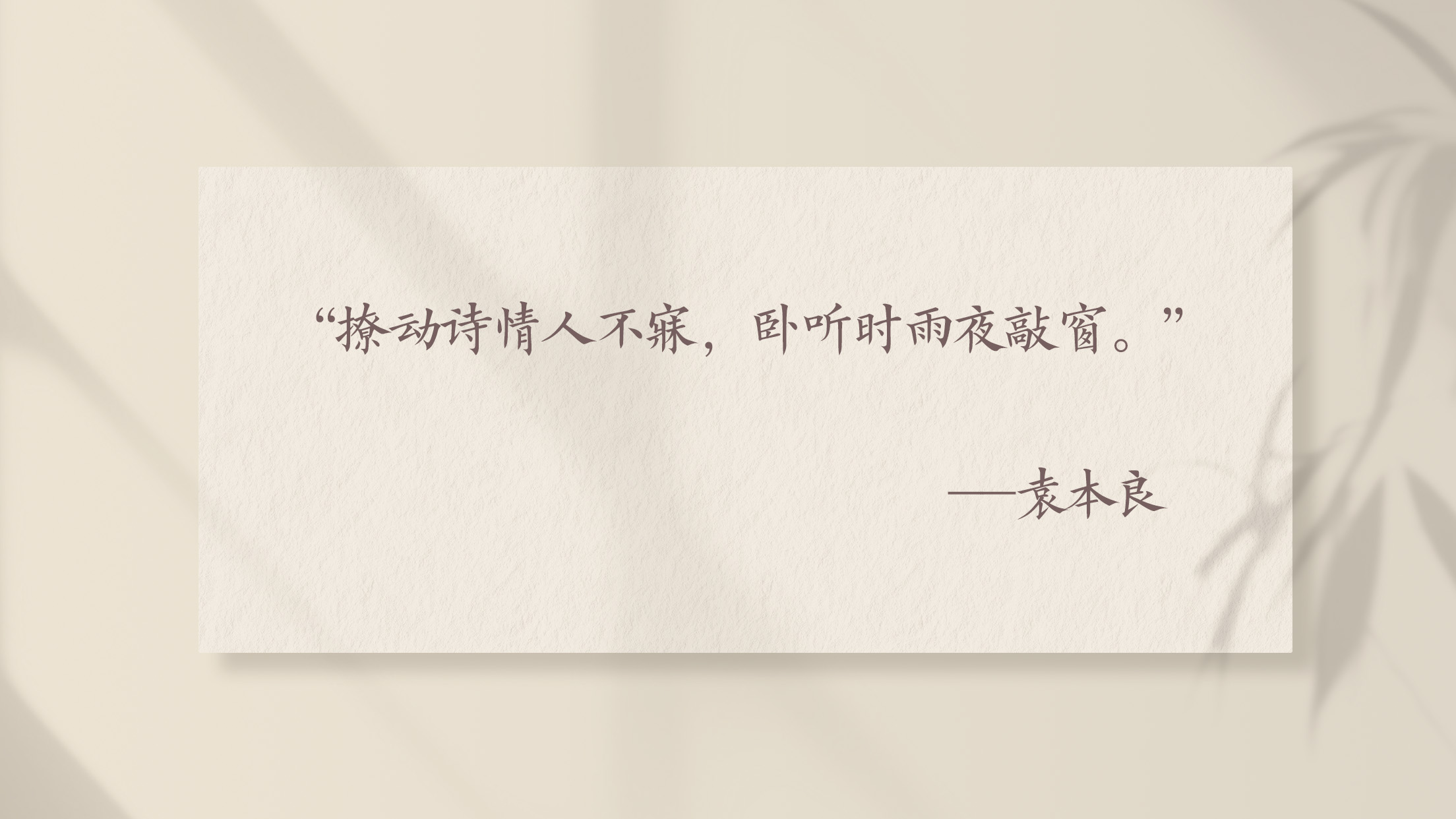
拿他与我之间的关系来说,几十年来,不管时局和所处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始终心灵相通,彼此挂怀。不久前出版的《书不尽言:钱理群书信集》中,收录了他在1981年至1997年期间写给我和妻子文侠的二十一封信。读着这些信,诸多既往岁月中所经历的故人旧事,以及其时其境下的所思所为,不由在脑海中浮现出来。信中对于我们生活、身体、工作和学问的多方面关切和慰勉,至今让人感动不已。
书信而外,我们也非常珍惜每一次见面的机会。理群兄曾写过这样的话:“而且我每次回到贵阳、安顺,本良也总是把我接到他的家里小住,并且总有深夜长谈,别处不可说,不便说,或者说了也不能理解的话,可以在这里畅怀、放情一说,说得眼湿润、心滚烫,说不出的舒畅,豁亮。”回想起来,20 世纪 90年代以后,理群回贵州大概有十来次,我几乎每次都有诗为记。“珠榴初绽柳丝长,老友重逢共举觞。梦里关山尝隔路,鬓间岁月又添霜。神追往事犹今事,心系兹乡胜故乡。撩动诗情人不寐,卧听时雨夜敲窗。”(《为理群兄返黔作》,1994年6月)“三月花溪迓客来,客来最喜菜花开。几回遐路从君梦,今次惠风入我怀。世事多艰难遂意,余生有幸且倾杯。夜谈相嘱同珍重,疏发难禁岁月催。”(《理群来筑夜宿敝舍》,2002年3月)“霜降次日天云黯,凉雨淅沥叶飘乱。理群冒雨来花溪,倒屣终慰数日盼。应国何幼与同行,驾车携囊共陪伴。明贤兄嫂枉驾来,难为平素深居惯。重逢纵是秋雨天,相见却是春风面。老友暌违二载余,怀念情肠何缱绻。旧梦新梦话题多,倾谈终朝浑不倦。”(《戊子八月理群来筑敝舍小住》,2008年10月)这些诗句,记录了我们在艰难世事中相知相恤的情愫,更是我们间特殊友情的一种纪念。理群兄曾说到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是“超越了一般所说的‘友谊’,而都成为对方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做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了”。我也曾对他说过,我与他的相知相得,“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之交,而是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上的一种追求和渴望”(2007年4月18日致理群函)。
上引2008 年 10 月诗中说的“旧梦新梦”,指的是其时已经编写出版的《贵州读本》和设想要编写的《安顺城记》。这就说到了理群兄对于贵州及安顺地方文化建设的执着追求和特殊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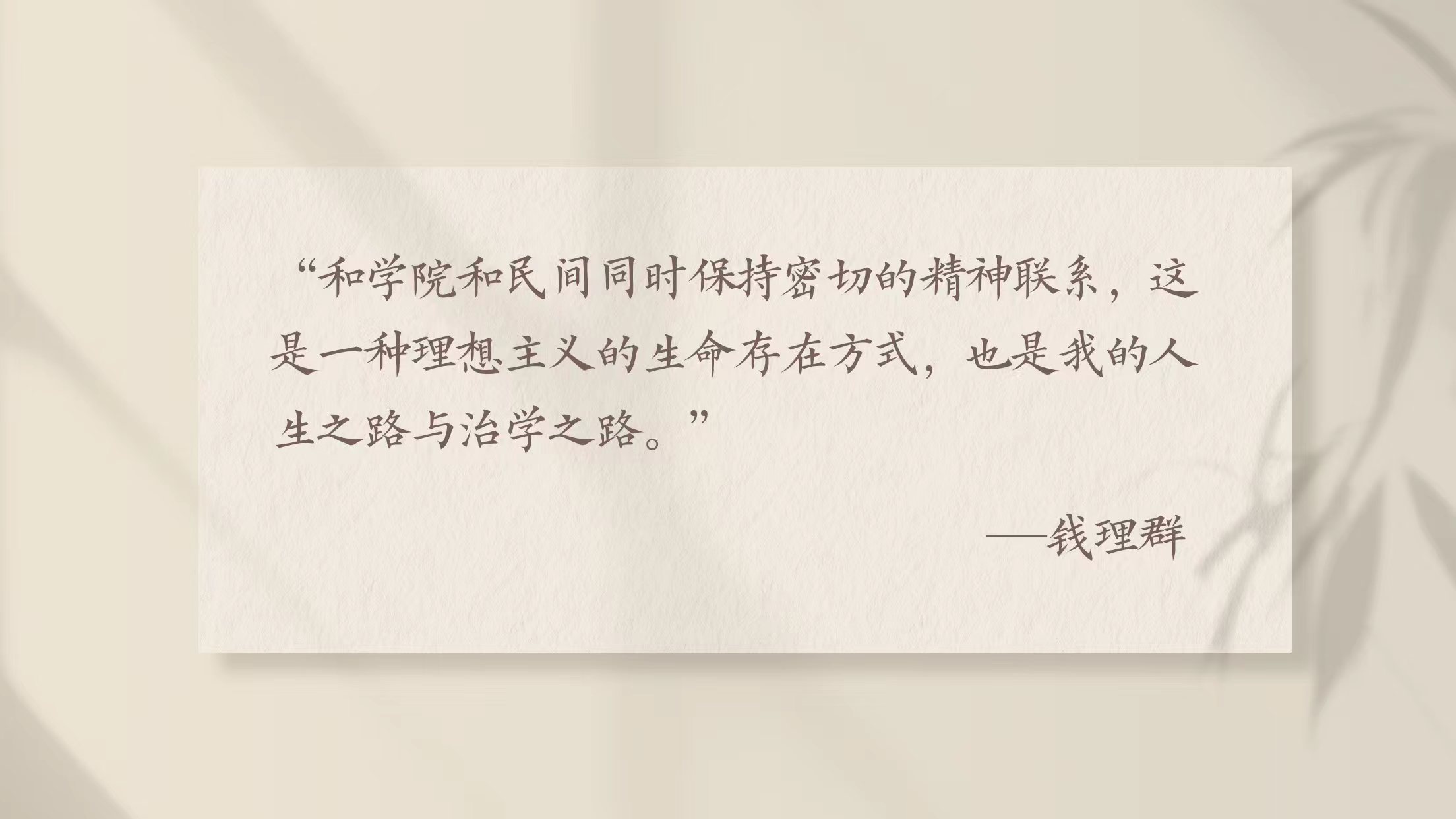
众所周知,编写《贵州读本》和《安顺城记》都是出于理群兄的设想和倡议。他曾经这样谈到《安顺城记》由梦境变为现实的过程:
《安顺城记》最初是我一个人的梦。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也到处讲,我到老年形成一个习惯:每天早上要早醒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静悄悄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就做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梦,其中最大的梦就是写《安顺城记》。梦开始的时间是2004年11月2日,已经有十年了。
按照我的习惯,有梦通常要先和杜应国交流:“小杜啊,我又做了一个《安顺城记》的梦。”他立刻表示赞同。于是就成了我们两个人的梦。他还写了篇《〈安顺城记(或史记)〉构想脉络》,以“录此存照”。
大概是在2008年的时候,在袁本良家里,跟本良和明贤先生交谈,又提起了编写《安顺城记》的计划,他们都觉得这一设想有点意思。于是就成了我们四个人的梦。本良有诗为证:“旧梦新梦话题多。”记得在场的还有孙兆霞,后来就委托她去落实。兆霞找来找去找到了省文史馆的顾久先生,编写《安顺城记》就成了文史馆的梦,这也就找到了实现梦的关键环节,有了组织者。之后又找到了贾正宁、高守应,安顺市社科联也成了实现梦的推动者。于是,终于有了2012年10月25日编撰预备会的召开。这是从一个人、几个人的梦,变成一群人的梦,这是由梦想到实现的决定性的一步。
《安顺城记》编撰预备会是 2012年10月25 至27日在贵州省文史馆召开的。26日晨,我有一诗奉理群明贤应国并示与会诸友:“老钱惯在梦中游,有梦十年回贵州。读本已圆乡情梦,城记又为故土谋。难得好人做好事,或期青史豁青眸。左迁神笔凭追摹,古道习安景色幽。”(《理群回黔纪事四首》其一)29 日,理群及应国夫妇下榻敝舍,30 日明贤夫妇前来,诸人畅叙终日。我也有诗为记:“守拙斋中故友逢,寒秋竟若坐春风。兴高旧梦赓新梦,识远钱兄与戴兄。户外风轻云淡淡,席前酒暖意融融。可期协力完城记,来岁筵开再一觥。”(《理群回黔纪事四首》其四)
记得原先的设想是两三年中完成《安顺城记》的编写和出版,但事实上这部七大卷的书到了2020年末才得以面世。从2004年老钱的梦开始,到 2012年编撰预备会的召开,这部书经过了八年的酝酿;而从启动编写到正式出版,则经过了又一个八年。这说明老钱所说“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的不易。在这个过程中,安顺、贵阳的参与者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总纂杜应国兄更是全身心地统筹编写,调查采访,组稿改稿,呕心沥血,个中烦苦不堪言说。而在整个编撰过程中,从拟定编撰主旨、整体架构、材料取舍、行文风格,乃至书稿中字词正误这样的细节,理群兄更是自始至终投入他充沛的精力和睿智的创意。这自然是他做事的一贯风格。《安顺城记》是如此,前期的《贵州读本》也是如此。从收入这本《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第一和第五单元的各篇文章中,我们都可以充分地看到这一点。
倡议并主持编写《贵州读本》《安顺城记》,是理群兄为推动贵州地方文化建设所做的两件大事。尤其是后者,这部他和众多乡友“竭尽全力,耗尽心血,整整写了八年”的大著作,其所体现的关于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研究的全新理念、全新追求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越了叙写安顺历史本身。作为一部“小地方、小人物支撑起来的‘新史学’尝试之作”,它为当下社会环境中的民间修史提供了成功的样本,同时也为“学院学术”与“民间学术”之间的跨界融合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理群兄曾说:“和学院和民间同时保持密切的精神联系,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生命存在方式,也是我的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正是理群兄对于自己人生之路与治学之路的一个方面所做的总结。
从这种对于人生之路、治学之路的自觉清醒的认识出发,理群对于贵州地方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寄以关切并引发思考。
本书中的第二、三、四单元,从贵州文化的历史到现状,从地方文学到教育,从屯堡文化到乡村建设,从文化谱系的整体构建到作家的个人创作,可以说是相当全面地涵盖了地方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在这些关切和思考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位思想者和文学研究者的诚挚情感,以及在学术中投入生命的独特目光。举例而言,读戴明贤著作,他看到了“笔端又流泻出更多的来自世俗生活与生命本身的元气”,以及“不放不收,亦放亦收,不平不奇,亦平亦奇,不庄不谐,亦庄亦谐,不俗不雅、亦俗亦雅”的为文风格,并由此发现了“小城人永远不变的散淡、潇洒的日常生活”,“小城人看惯宠辱哀荣的气定神闲的风姿”,“是这城这人所特有的韵味”。读韩乐群的诗,他因老友“没有被苦难的历史压倒,在晚年招回了自己的魂”而欣喜,并因“这同代人的凤凰涅槃”而“从绝望中看到微茫的希望”。在对篮子(杜应国)们的“思想寻踪”过程中,他认为“这些精神的困守者是在与中国大地的困守者,生于斯、耕耘于斯、死于斯的普通百姓合为一体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意义的”。因此由衷赞美他们那种“无言的伟大,卑俗的崇高”(篮子语),并发出呼吁,对于这种“在比我们这些学院的思想者艰难、恶劣得多的环境里的思想、文化的坚守”,“是应该引起更多的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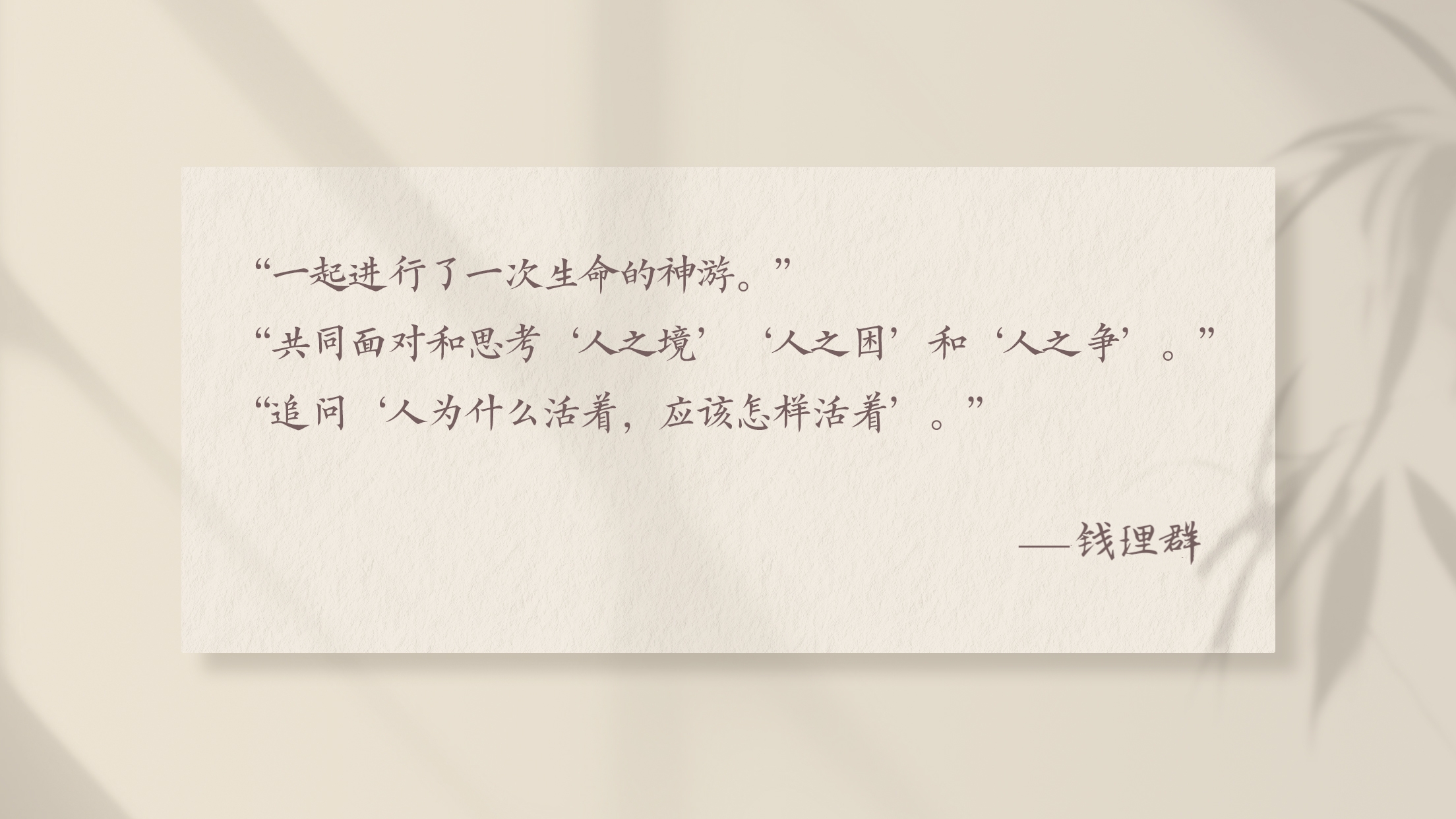
收入这几个部分的文章,很多都是为贵州朋友所写的序或评论。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理群写这类文章,总是把自己“真正投入其中”。他“不是简单地写序,而是要和作家本人,更是和贵州的父老乡亲、山野生灵,进行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在本书第三单元,我读到了此前未曾看到过的一篇序文。这篇写作时间将近一个月(“2020年6月27 日一7 月 24 日写于封院中”)的序文,是为他的学生、安顺作家罗银贤的文集所写的。理群在这篇序中追寻了作家从山野生命走入现代文明殿堂从而获得更新的“更加广阔的心灵的家园”的过程,在对其“戏里人生”(戏剧创作)和“山野心灵”(小说创作)进行探讨的同时,和作者“一起进行了一次生命的神游”,“共同面对和思考‘人之境’、‘人之困’和‘人之争’,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这篇三万余字的长文,是理群兄在考察贵州文化时完全投入自身、由人及己而又推己及人的研究特色的充分体现。罗银贤是安顺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又是与理群关系亲密的几个弟子中的一个,曾经和我也非常熟悉。理群说,他写这篇序时,觉得“突然面对一个我其实并不了解的罗银贤”。读了理群的这篇序言,我也感到以前觉得熟悉的小罗实际上非常陌生。在这篇与作者一同进行生命神游的序文中,理群所投注的并不仅仅是源于师生亲密关系的情感因素,更多是投入了学术研究中的自我参与理念。正因为如此,才能与作者一起去发现他“心目中的文学创作”,发现生命文学的“特殊价值和魅力所在”。
本书的第六单元“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再出发”,其中所收的两篇讲话稿(2021年12月在北大中文系,2023年6月在“天下贵州人名家大讲堂”),集中体现了理群兄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所谓“再出发”,在他看来,就是要向构建“安顺学”和“贵州学”(即“黔学”)继续迈进。为此他提出了诸多设想和建议。他直言这些设想和建议“都带有极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是我的本性,改不了,也不想改:我总是在不断地‘做梦’”。我们大家都知道,安顺和贵州地方文化研究得到的这些成果,许多都得益于理群兄的“梦”。他总是“旧梦未去,新梦又来”。并曾自嘲说:“在爱做梦这一点上,我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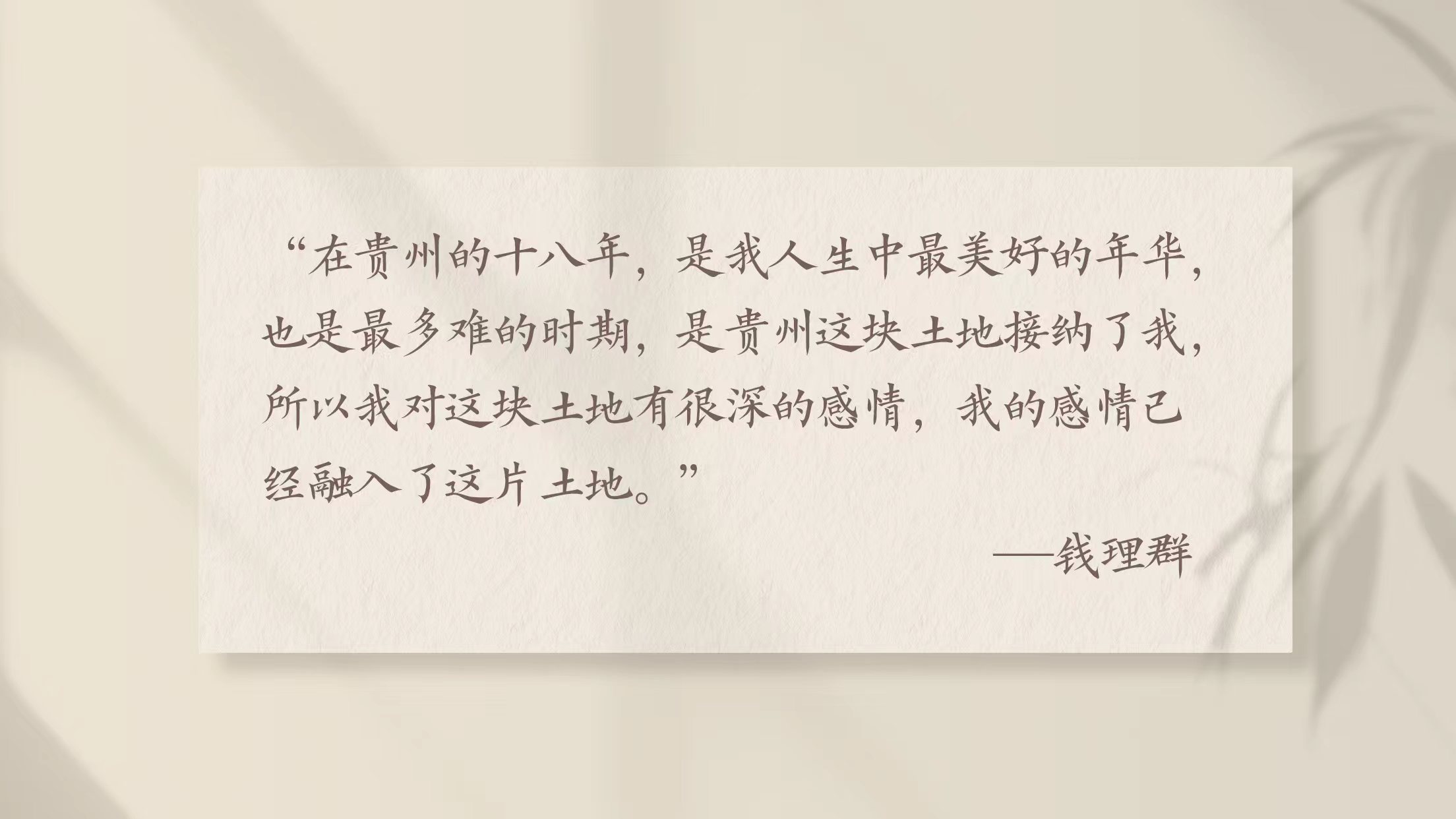
理群兄的确很爱做梦。我在这里想引述理群兄的一次讲话。正好是二十年前《贵州读本》出版,理群兄曾受贵州教育厅之邀,在贵州的几所大学作巡回演讲。本书所收他在贵州民族学院的讲话中有这样一段:“在贵州的十八年,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也是最多难的时期,是贵州这块土地接纳了我,所以我对这块土地有很深的感情,我的感情已经融入了这片土地。1995 年我在韩国当客座教授,夜里做梦,回到贵州,得诗一句——‘梦里万家竹楼’。因为我不是诗人,得一句就写不下去了,我把这句诗寄给我的好朋友,贵州大学的袁本良教授,请他补足,结果他寄回一首《西江月》:‘眼底星星渔火,梦中处处竹楼。他邦竟作此乡游,许是汉江雨后?惯看烟岚出岫,曾谙水上凫鸥。何时携手再寻幽,共赏夜郎春透’此次来,就是来携手再寻幽。”理群兄身处北大,不忘贵州、安顺的故地老友,在多次的“做梦”而又“寻幽”中,为构建贵州和安顺地方文化付出了全身心的努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既令我们这些贵州乡人感念,同时也让国内外学术界瞩目仰佩。理群说,他和乡友们一起努力所做的,“不仅是一项学术工程,更是一种情感的投入,一种生命的投入”。贵州和安顺的历史将永远记得这些努力和投入的特殊意义。
理群兄曾两次为我的书写序,除了收入本书的《我们的坚守和追求——读袁本良〈守拙斋诗稿〉的断想》外,还有《旅游,风景的发现和行旅诗——读袁本良(诗里游踪:我在白云边)的浮想》,这是一种友谊的纪念和馈赠。说来惭愧,作为他多年的至交好友,我从没有为他写过一篇文章。记得多年前曾想写篇文章谈谈读他著述的体会,用以报答几乎每书必赠的厚谊,但因为疏懒,文章终未写成;其后也再未生此念想,原因是我常对他说起的“我们的阅读速度远远赶不上你写书出书的速度”。这自然是一种自我开脱之辞,实际上心中一直抱愧。现在,理群兄的这本《认识脚下的土地——关于贵州地方文化研究的思考与讨论》即将出版,嘱明贤兄、应国兄和我各作一序,我为终于有机会略作报答而高兴。不过,我对于贵州地方文化可以说是知之甚少,除了参与《安顺城记》这样的集体项目之外,平素对地方文化留意不多。受命写序,不禁忐忑惶恐。以上所写,文字拉杂而见识浅陋,自是有负雅命。不过,我知道理群兄嘱序的用意,不过是为了给我们间的友谊留一纪念而已。如此想来,这篇序文写成什么样子,好像也就无所谓了。
兹序草成,有感而赋《卜算子》一阕,以此向理群兄及所有关心支持贵州地方文化建设的朋友致意。
旧梦尚萦萦,新梦翩翩至。梦绕魂牵若许年,总为黔山事。读本已宏涵,城记何渟峙。漫道功成梦已阑,再展高飞翅。
2023年12月18日写毕于三亚山屿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