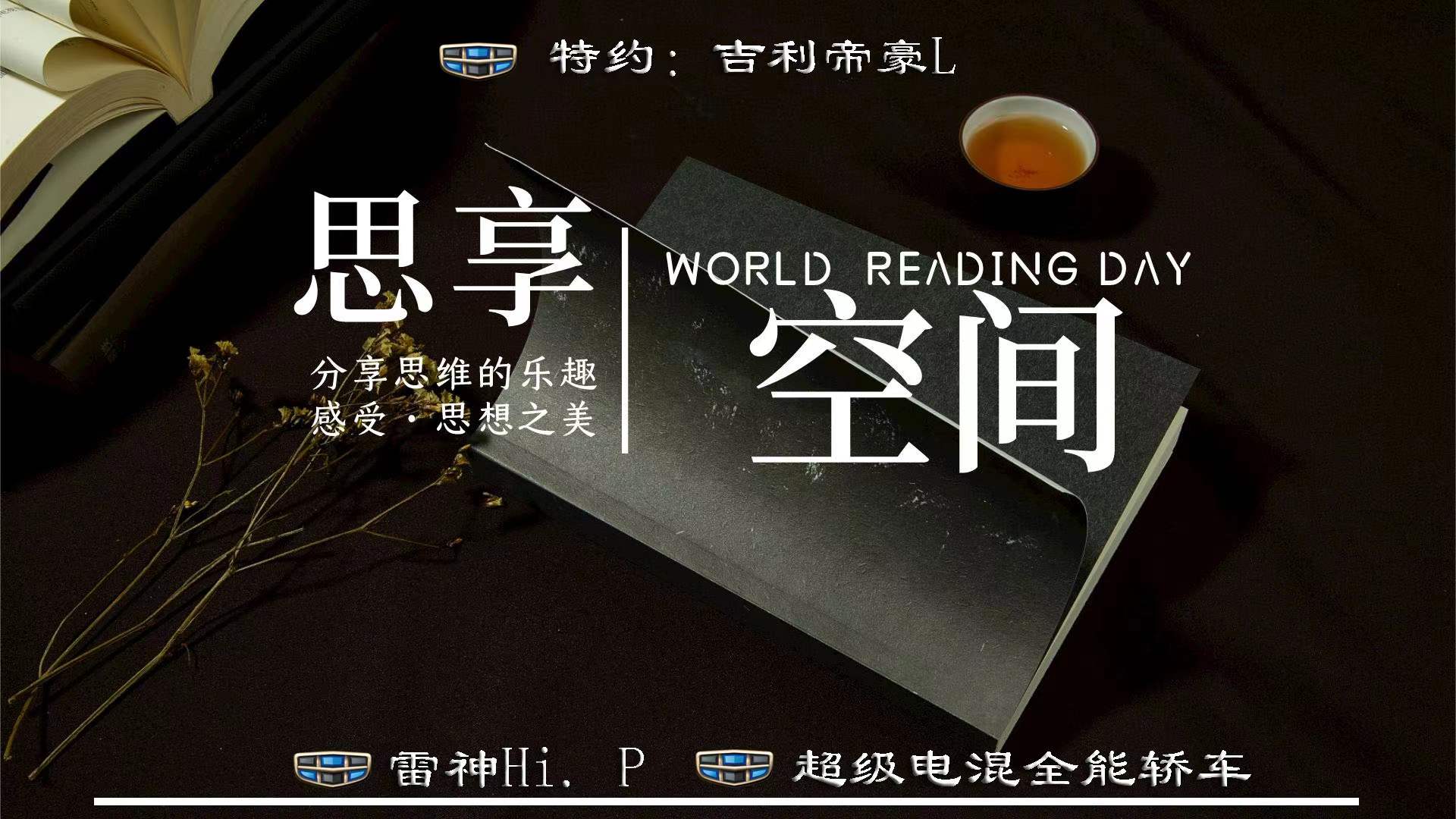思享空间·叙谈录丨你会如何记录,你穿行而过的时代?


我们既是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也是历史的书写者。
个体的回首、驻足,匆忙中描绘着这个轰轰烈烈、向前奔腾的时代。
或许未来,今日的一切也会成为新书的章节。我们所穿行的时代,终将由我们自己记录。

小崔23岁那年,坐绿皮火车折腾两天一夜,北上哈尔滨,只为看一眼传说中的太阳岛。
松花江江水苍茫,岸边野草疯长,太阳岛只是江心一片草甸,小崔大失所望。他因那首《太阳岛上》慕名而来,但眼前并没有歌中的泳装与姑娘。
多年后,歌曲作者王立平说,他也没上过太阳岛,那首歌唱的是阳光,是无数普通人心中的向往。
那个年代的故事往往通过歌曲留存。《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收纳着青春奋斗,《请到天涯海角来》记录着闯海雄心,崔健粗砺的《一无所有》中,有一代人的坦然与无畏。
1987年,《歌曲》月刊编辑陈晓光,到四川温江采风,傍晚时分,炊烟袅袅,农舍远处是广袤的田野。他有感而发,写下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一代人的澎湃从此寄托在旋律里。
歌声成为我们的记忆坐标。歌手蔡大生说,每当听这些歌,就穿越回少年时,“阳光普照,真诚干净”。
阳光之后连着春光,1992年,黑龙江退休职工蒋开儒,南下闯深圳。他踩着摩天大楼的影子,听着发动机的轰鸣,汇入奔跑的人潮中。
那年11月,他写了《春天的故事》,第二年传遍大江南北。多年后,他打车司机听说他是作者,兴奋放歌,说第一次来深圳的人,听到这首歌,话就会多,人也会亲近起来。
人们在歌声中寻找着时代的共鸣。《亚洲雄风》唱着打开国门的骄傲,《东方之珠》唱着百年回归的期盼,《相约九八》在落雪的春晚舞台上,眺望着一个新的世纪。
《一封家书》的平凡字句之下,是千万人的心语倾诉;那年秋天,北京丰台5平米平房内,王旭和刘刚在宿舍铁床前,光着膀子,纵情唱起《春天里》。

1999年,导演王兵开拍纪录片《铁西区》,初衷是“拍摄那些没有看到自己存在的人们”。
歌声只留时代的侧影,影像则有更丰满的细节,普通人也可以做主角。
王兵带着租来的DV,回到沈阳,用4年时间奔走在工厂、社区和街道间。一代东北人正在穿行他们的时代,风急雪冷,小人物的故事被留在镜头之中。
画面里,工人们穿行在工厂的酸雾中,买着两元一张的彩票,拿着工资,看着工厂烟尘弥漫铁锈色的天空。他们的故事以这样的方式凝固。
豆瓣上,有年轻人把纪录片下载后,搬着电脑,给他当过冶炼厂工程师的姥爷看,“七十多岁的老头儿看完后哭了”。
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之外,普通人的故事更打动人心,因为足够真实,连缀起来就是人间。
拍完《舌尖上的中国》多年后,陈晓卿拍了续作《风味人间》,美食已退居其次,重心是人间。
在葫芦岛,他们拍了渔民老六。老六是仅存不多的赶海人,他穿着胶裤站在海潮中,唱着“我醉提酒游寒山,霜华满天”。
他对着镜头总结人生,年少轻狂,有煮酒英雄梦;青年意气风发,搞大船出远洋,赔得一塌糊涂;人至中年,浮沉半生,最后只想守好这片海。

歌声承载信息有限,摄像机无法穿越时空,最后依旧是文字,能连接远去的时代。当年轻一代提起笔,历史展开了更多的维度。
三年前,网文作家“眉师娘”的大伯去世,悲伤之余,她萌生想法,写一本网络小说,留下大伯的故事,以及那个奔腾的年代。
“眉师娘”的大伯,以及其他父辈,都是第一代闯海人,八十年代,他们从江浙小城出发,一路向南,去海南寻梦。
1998年出生的“眉师娘”,从小就听那些闯海的故事,听故事多是傍晚,往事最后沉入夜宵的酒里,散入傍晚的风中,让她念念不忘。
她提笔写父辈的故事,书名定作《奔腾年代——向南向北》。简介中她写道:小人物的沉浮,串起一代人的奋斗成长,汇聚成我们的奔腾年代。
在起点,类似的创作者还有许多。北师大的副教授齐橙,在起点第一本小说名为《工业霸主》。那年他刚四十不惑,在课堂上讲新中国经济序列,看学生们眼神溃散,便灵机一动,把工业节点串成故事,学生们听得心潮澎湃。
他由此萌生用网文的壳,讲工业历史的想法,并一发不可收拾,《工业霸主》后,他又写了《大国重工》,“只有冰冷的机器,才是国家发展的基石”。
这不仅仅是一本小说,故事中大到国家预算,小到饭菜价格,齐橙都查阅大量资料考证还原。最后的硬核故事,像琥珀般凝固了那个激情的年代。齐橙找印刷厂把故事打印出来,A4纸摞成10厘米高,里面是沉甸甸的岁月。
越来越多人加入讲述者行列,他们不仅记录过去,也书写当下,记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后的今天,记录中国当代的方方面面。
作家“半部西风半部沙”从事合成纸设备研发,受《大国重工》影响,他写了《大国机修》,通过小人物故事,展示中国机械制造业的征途。
作家“人间需要情绪稳定”,则是在巴黎老佛爷百货橱窗里,看到了中国数码产品,受启发创作了《破浪时代》,借国产通讯设备故事,讲述中国通讯业发展史。
无数人提起笔来,书写在历史的空白处。那些属于普通人的故事,从此不会消散在时光中。它们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疫情爆发初期,网文作家“真熊初墨”写了《医者无眠》,现实中他是三甲医院的医生。
写书期间,他书中人物原型,大年初三就到武汉协和支援抗疫,而那本小说,也从爽文路线,变为琐碎的方舱日常。
书评说,从小说角度,这两百多章情节拖沓,但从现实角度,那是宝贵的疫情写照。
那些走家串户的社区员工,抱着体温计帮忙守路的志愿者,奔波海外邮寄抗疫物资的留学生……我们穿行的时代,留在段落间。
小说结尾,武汉解封:
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手持烟雾机,像未来战士、又像机体里的巨噬细胞一样,为这座城市最繁华的火车站,进行最彻底的消毒。

岁月的年轮前进的同时,每个人都在书写着自己的故事,不管真假不论悲喜。曾经的过去会换一种方式重演,不变的是不管怎么演都会有观众。我以我心看时代,我以我笔记录之,但愿,未来会有人记得我们是如此地坚强。
——小可
文本参考:《摩登中产》——那些写玄幻的笔,正在写奔腾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