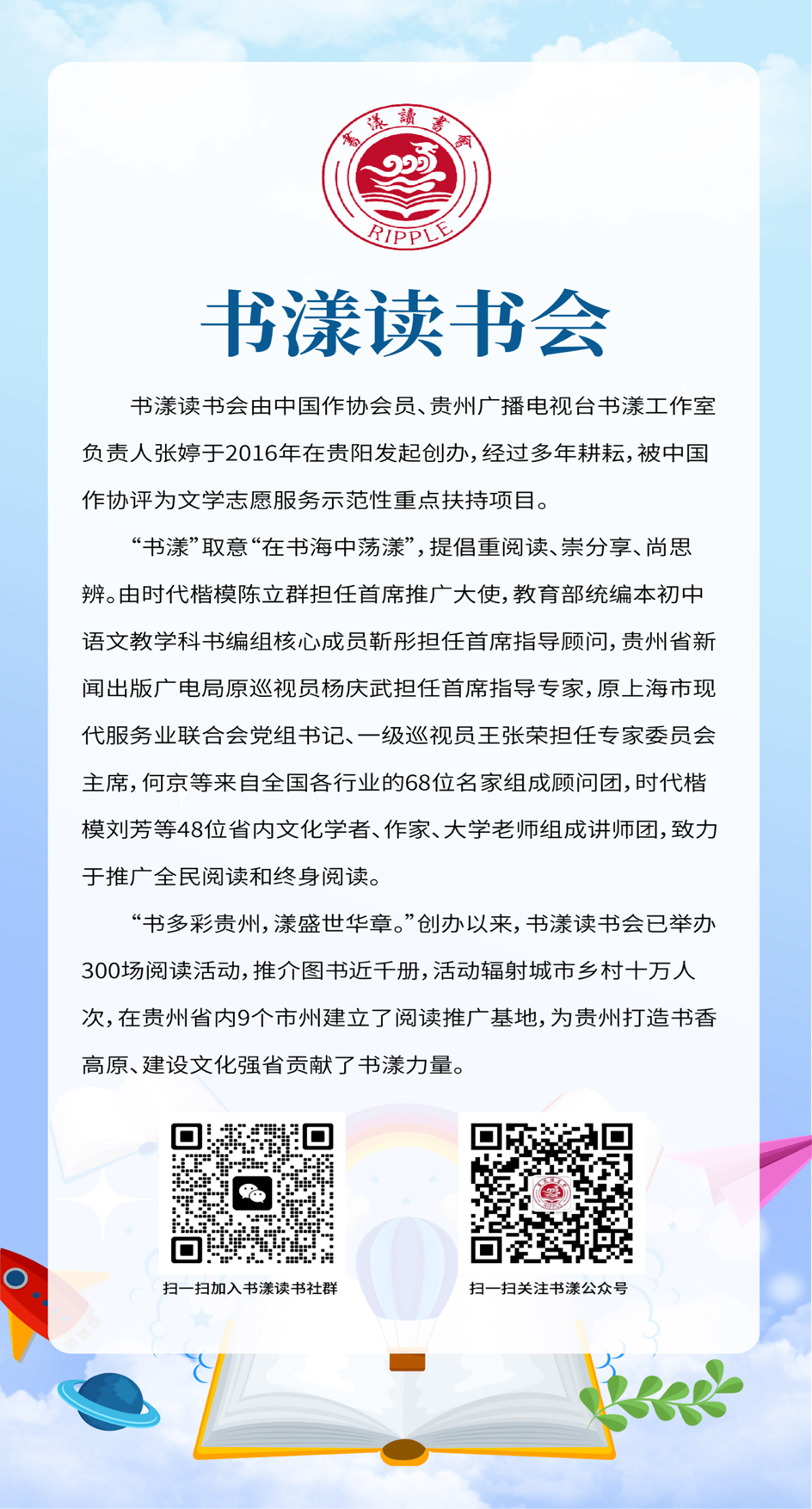动静荐书丨书写人性的光辉——论若非小说集《十二盏微光》
《十二盏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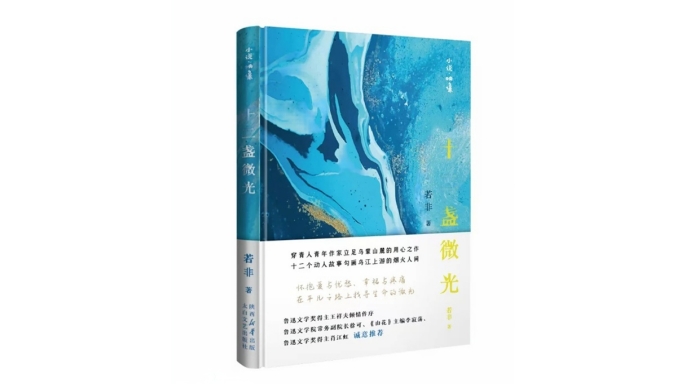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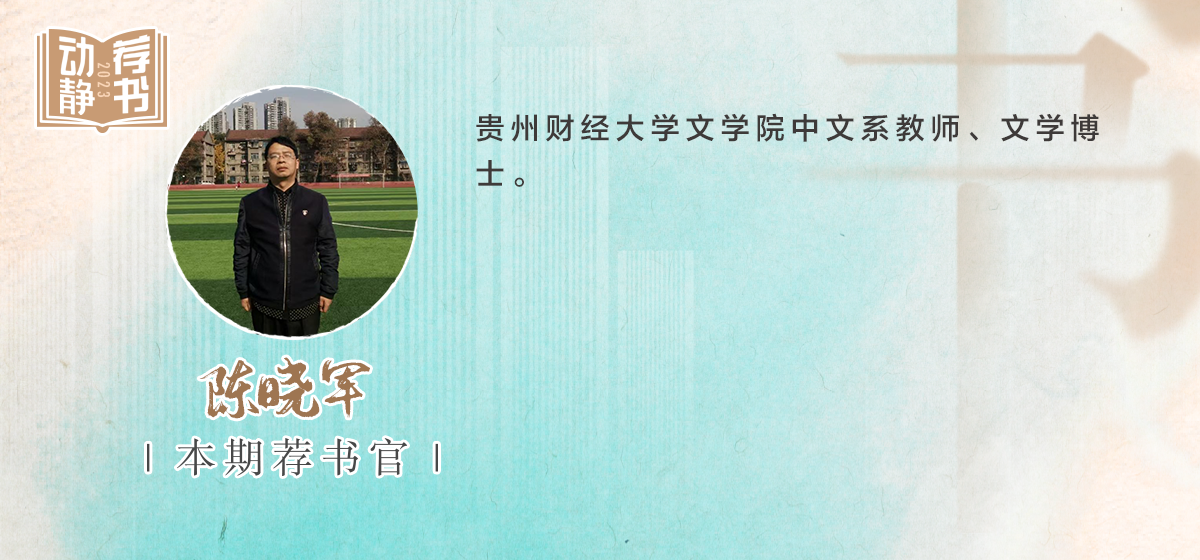
贵州青年作家若非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十二盏微光》,聚焦黔西北乌蒙山麓的烟火人间,书写平凡乌蒙人在时代变迁中的爱与忧愁、幸福与疼痛。在主题思想、人物构造、叙事艺术、象征运用等方面均有可圈点之处,显现出作者对小说这一文体深入的理解和熟练的掌控力。
《十二盏微光》的共同主题是揭示人性善良的一面对处于种种困境中的人们的价值和意义。小说的思想丰富而深刻,善良与责任、困境与救赎、亲情与成长是小说关注的核心话题。《溢补嗒启》讲述齐桑与林夜生的故事,探讨了爱情、责任、家庭和个人选择的复杂性。《嘎依的来信》通过策云的经历,深入探讨亲情、爱情、人生意义和救赎与重生的主题。《李元生》通过乡村教师李元生的故事,展示了教师的责任感与学生艰难的成长历程。《夏日的回响》通过林诗英和铁头、芋头的故事,书写了困境与救赎的主题。《晚课》通过铁头、芋头和戴菲菲的和老路相遇的故事,探讨成长中的迷茫与觉醒、迷途与救赎。《大河东流去》深入探讨了社会偏见和爱情的神奇。《倒立》以男孩铁蛋的成长过程为主题,也是一个以救赎为主题的故事。《回煞记》探讨父女间的亲情与爱。《告别的事》对爱与亲情及人的命运等话题进行深描,赞颂生命在行进中的韧性。《十二花园等你来》书写了乡村留守未成年人和老人对爱和关怀的渴望。这些主题与当下社会中人们关注的经济、社会、文化、城乡、家庭等热点话题密切相关。
正是在对当代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和把握的基础上,若非构造了与当代社会关系密切的众多人物形象。《溢补嗒启》成功塑造了在爱情和事业中挣扎的内心矛盾的青年乔桑和因负罪离乡一生处于悔恨之中的林夜生这两个人物形象。《嘎依的来信》塑造了面对困境迷失方向的策云和嘎依及其家人善良而坚韧的形象。《夏日的回响》塑造了铁头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形象。《仁心》讲述乡村医生赵友良在张老三成长中的意义,两个人物的描绘可信感人。《晚课》塑造了老路这一给人深刻印象的人物,铁头的转变也真实可信。《李元生》塑造了一个叫李大嘴的有责任感的但并非完美而逼真感人的乡村男教师形象。小说还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女性形象,如《告别的事》中外省嫁来的女人坚韧、温柔、深情的形象,《回煞记》中的女儿形象。作者还塑造了一些社会边缘人物形象,如《大河东流去》中的叔叔,是一个孤独、坚韧的形象。《十二花园等你来》描绘了等待亲情和关心的乡村留守未成年人张老大、大牛和老人孤独、无助、脆弱、善良的形象。《暖春将至》书写了移民搬迁中进入城市生活的农村老年人面对生活变迁的迷茫与挣扎的老人的逼真形象。
这十二篇小说故事精彩,叙事视角多变,细节精微,情节编织巧妙。《告别的事》运用意识流和蒙太奇手法描绘苦难、回忆和等待,营造了独特的美学氛围。《晚课》中的“套中套”构思,使得情节跌宕起伏。《溢补嗒启》通过两条线索交织,推动故事发展,并在情感转折点上引起读者共鸣。《嘎依的来信》以策云的生活困境开篇,通过信件展现了人物内心世界,并在策云前往毕节寻找真相时达到情感高潮。《李元生》巧妙地以“我”的视角叙述,通过中断和继续的手法增强真实感。《夏日的回响》故事复杂而丝丝入扣,人物成长真实可信,结尾点题,打动人心。《仁心》有紧凑的情节设计,汪老三的成长符合心理逻辑。《回煞记》小说情节紧凑,叙述流畅,巧设伏笔,回忆的穿插流畅自然,父女间的亲情细节书写感人。《十二花园等你来》的乡村生活细节描绘完美地显现人物的心理,大牛求助于坟墓里的父亲、张老大梦中老是出现泥鳅这些细节的真实感使小说产生了丰厚的情感张力。《暖春将至》的闪回穿插和细腻的心理描写,成功地带领读者深入人物的情感世界。《大河东流去》以叔叔救人的英勇行为开篇,吸引读者并设置悬念,被救女子的出现揭开叔叔断手之谜,故事达到高潮。以人物的感情流动为线索串联拼接起复杂而丰富的事件和情节,若非成功地获得了在时空中的自由转换、掌控着读者心理的权利,由此可以说,若非是一个合格的“故事造型师”。
作为一个善于捉弄象征的具有诗歌写作经验的写作者,若非通过标题的构思设计和故事中人物的命名,以丰富的象征意象赋予了这些小说以美的内涵。《溢补嗒启》中的“溢补嗒启”不仅是地名,也是与三个爱情故事紧密相关的空间,使得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得以并置对照,提供丰富的审美体验。《回煞记》中,女儿与父亲成为象征符号,表达了人类情感的相互依存。《夏日的回响》中,“夏日”不仅是时间概念,也是承载主人公回忆与成长的容器,象征着难熬的青春。《大河东流去》中的“大河”既是实际的河流,也是叔叔情感和个性的象征。《十二花园等你来》借助“花园”意象,比喻留守未成年人这一需要保护的群体。《倒立》中的“倒立”不仅是铁蛋的特殊技能,也是看待世界的另一种视角。《嘎依的来信》中的“嘎依”象征着乡村的美好人性。《暖春将至》的“暖春”象征着季节变化和主人公内心世界的转变。《晚课》的标题与主题和情节紧密相关,老路的故事成为高潮和转折点。《告别的事》“血鸭”不仅是食物,更是表达女人与丈夫、儿子情感的纽带。此外,作者还巧妙地通过人物命名传达象征和寓意:《李元生》中学生们把老师叫“李大嘴”,既描述了李老师的外形特点,也符合学生在未成熟时因对老师的某种轻视和讨厌的心理。《仁心》中的医生“赵友良”的命名直白地表达了赵医生的仁医形象,而“汪老三”这个被赵医生治愈的病人的命名的看似随意则象征着这样的被治愈的个体的普遍存在。《夏日的回响》中“林诗音”这个名字与某武侠小说中性格温柔的同名人物的形象和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形象形成互文关系,使得这一符号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晚课》中“老路”这一人物的取名具有他是铁头等人“指路人”的寓意。在《夏日的回响》《晚课》等三篇小说中,作者都给主人公取名“铁头”或“铁蛋”,这一符号显然意味着他们的难以教化的个性。有意思的是,《回煞记》和《告别的事》两个故事中的女主人都没有明确的名字而以“她”来指代,作者显然是有意而为之,意在传达类似的情感具有普遍性,达到“共名”的效果。
小说的一大亮点是书写了人间烟火中无处不在的人性的善良和温暖。《溢补嗒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细腻刻画,书写了爱情在每个人的人生中的重量,林夜生的情同此心,乔桑的转变,显现出人性的美好。《嘎依的来信》中小山村的嘎依及其家人对美好人性的坚守,给人以力量。《夏日的回响》中林诗音的善良引导铁头走出困境,《晚课》中老路的痛苦经验转化为善良的人性之光,《仁心》中乡村医生赵友良的善良唤醒了汪老三,《李元生》中的乡村教师李先生的善良,《倒立》中的二丫,《十二花园等你来》中的赵友良医生,都让我们感动于美好人性的光辉。《大河东流去》中多年后女子找到救过她的叔叔的传奇故事,表达了作者相信美好人性的坚定信念;《暖春将至》中张薇薇的温暖关怀,照亮了杨梦生人生的晦暗时刻;在《回煞记》中的女儿与父亲的生命意识互动,传递着丰富的人性内涵;《告别的事》让我们感受到即使在世界最偏远的角落,因为有爱,一个面对夫死子病的女人在生活中也能够获得重新出发的力量。
若非生长在黔西北乌蒙山深处,其个人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验直接地体现在这些小说之中,我们甚至可以感觉到他在书写这些与时代人心关系密切的故事时内心的深沉的感情。“写作即疗愈”,这些小说中,我们也可以感觉若非对与自己血肉相连的故乡人事的依恋和深刻审视,以及在表达倾诉后的解脱。这些小说无论是在生活的开拓和深入思考,还是在叙事和众多让人熟悉的人物塑造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阅读这些小说,可以给每个负重前行的读者提供疗愈的力量。
作者若非简介:

贵州毕节人,穿青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鲁迅文学院第四十五届高研班学员。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北京文学》《山花》《青年文学》《文艺报》《人民日报》等,获尹珍诗歌奖、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金贵奖”。已出版长篇小说《花烬》、诗集《哑剧场》等作品八部。
书友读后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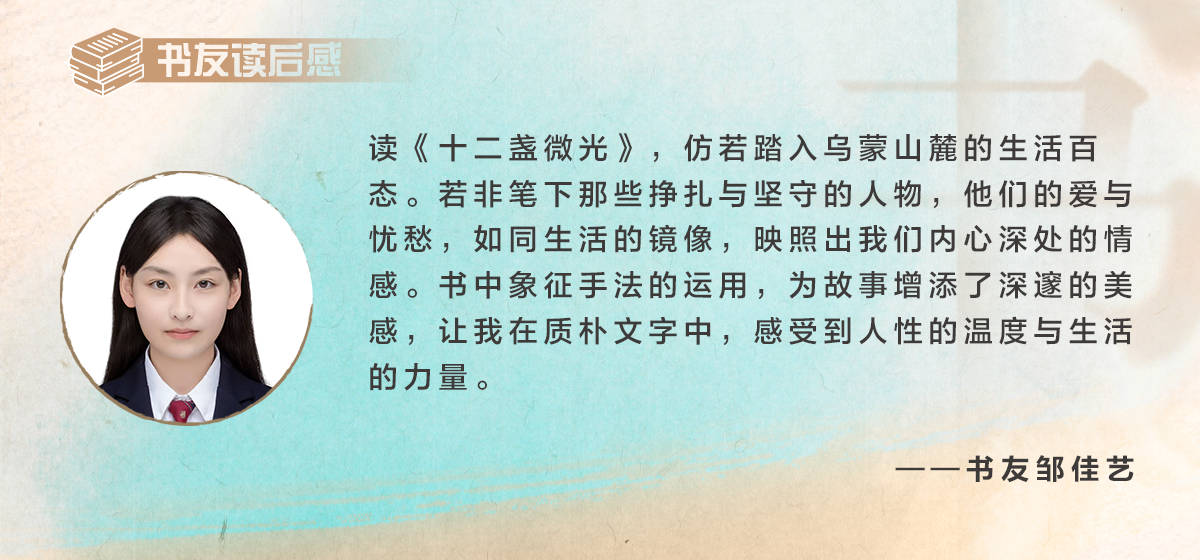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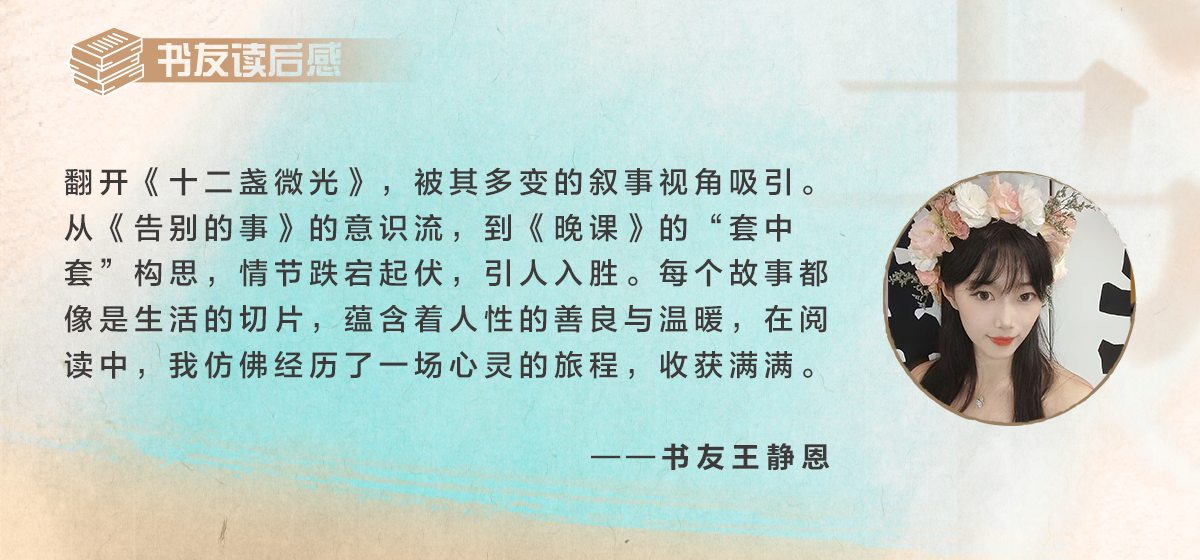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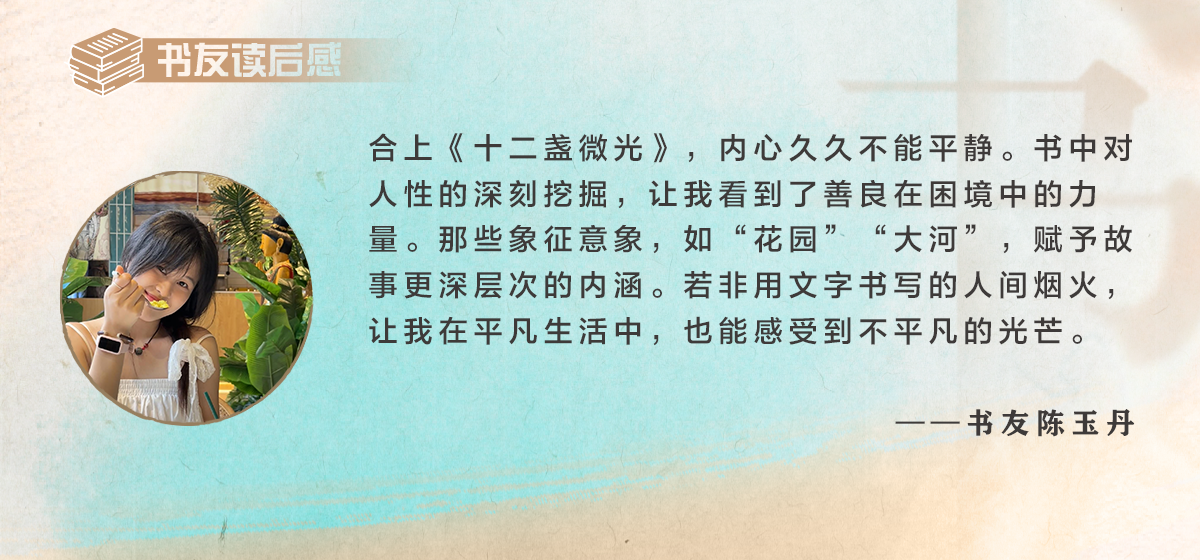
动静荐书合作伙伴:书漾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