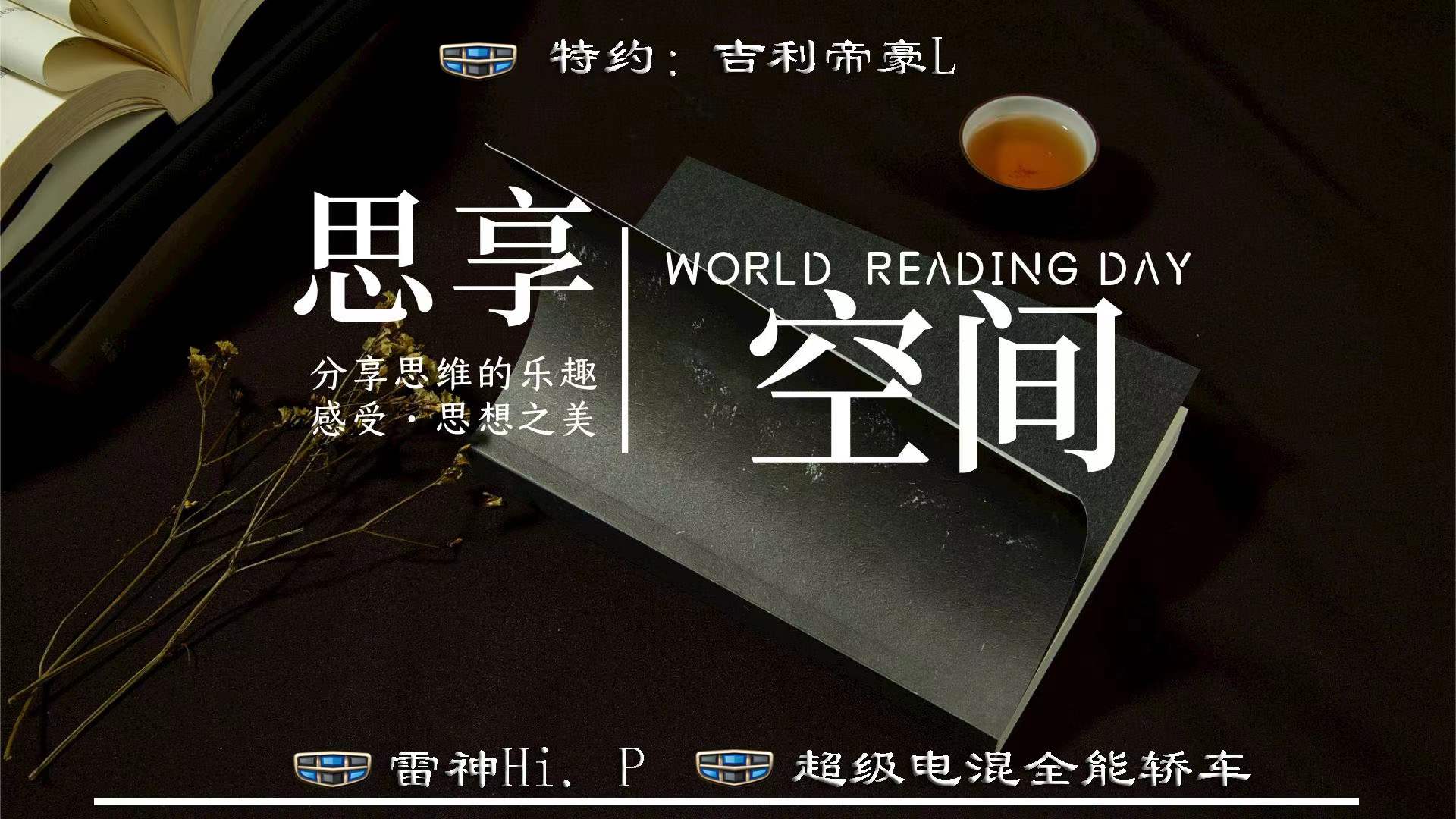思享空间·人物志丨许倬云——往里走,安顿好自己


2022年9月15日,92岁的史学大家许倬云用视频短片的形式为年轻人带来一场演讲——“如何与工作相处?”短片开端以独特的提问形式展开:“工作到92岁是一种怎么样的体验?”
许倬云娓娓道来工作对于他的意义,“工作不仅是维持你的生活,也是你和社会的一个连线。”
1930年出生,从纷纭历史中走过来的许倬云,由于身体的缘故从小无法正常站立,然而身体的桎梏并没有让他停止学习和探索。他近三十年致力为大众写史,著有史学作品数十种行世,海内外行销百万册。
做学问的人是没有年纪的。短片中,92岁高龄的许倬云坐在轮椅上,使用电脑浏览全球资讯,时至今日,他仍未停止工作。“工作中你可以获得许多知识,你可以获得许多人生该有的态度,我乐此不疲。”他认为:每次尽心尽力做好一件事,就等于雕刻一个艺术品,“工作是雕塑你自己”。

喜欢和年轻人对话
其实,许倬云一直对和年轻人交流保持着热情。
2022年刚刚到来的时候,许倬云录制了一段视频,在全世界被疫情所困的日子里,他有一些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
坐在家中的桌前,他双手交叠,唯一能动的那根手指一动一动——那是他说话时的习惯。这个生于战乱岁月的老人,平静地目视镜头,说:“我一辈子没有觉得哪个地方可以真正给我们安定,哪一天会真正给我们安定。”
在这既短暂又永恒的风云变幻中,他想提醒年轻的朋友,要记得反省“我自己有没有作为其中的一份子,促成了这个风云变幻,“不能完全安于说,我的日子好,就够了,我们每个人要想想未来该怎么做,要想想现在该怎么做。”
他相信年轻人,也能感受到,在这个纷乱复杂的时代,年轻人渴望向他寻求答案,“对他们我愿意舍得精力”。他相信个人行动的力量,想要告诉年轻人——责任不是你担社会责任,你担你自己该负的责任,你担你对你相处的人的责任。
后来他在《许倬云十日谈:当今世界的格局与人类未来》中说:“我盼望,我在世间走了这么一遭,有机会跟大家说这些话,使大家心里激动一点,本来平静无波的心里可以起个涟漪。小波浪可以造成大潮流,推动大家不断地、一天比一天进步。”

投向百姓的历史观
他喜欢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下很多人的关注落点——零碎。在这样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时间,给大问题做注脚的人越来越少。这十几年来,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波经常向许倬云请教问题,他们的话题既有古代历史、考古学、社会学等,也有时下流行的各种话题,比如内卷、躺平等等。
在持续经年的求教与讨论之后,王波说:“如果说我有什么治学习惯承袭自许先生,那可能就是历史思维。这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历史,不是被降格了的对历史事实的编年记载,而是建立在通晓人类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超越基于常识的经验思维,将历史本身作为根本原则,把握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他说,许倬云对于知识人的期待是——努力做能够“一锤定音”的人,起码要有这样的气魄。
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为许倬云所著《说中国》写解说,他感受最深的,就是许倬云先生的视角始终很宏大,但大视野投向的从来不是大人物。在他的目光里,小民百姓、日常生活份量深重。
1993年夏天,许倬云为在内地出版的《西周史》重写序言。他写下自己受到的质疑,“《西周史》问世以来,曾得到若干同行的批评。批评之一:居然连周公的事迹也不提!其实不仅周公未有专节,文王、武王、太公、召公……均未有专节。”
他回应道:“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在英雄与时势之间,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与推移。我们注意的是人的生活,从一个人看他的时代,他的悲欢离合多少是他自己负责任,多少不是他的责任。绝大多数的悲剧不是他的责任。”
正是这样的认知,构成了他与一般史家不同的治学特点。在这部史书中,他着重探究的是周人天命观念的形成,又另辟章节描写周人的生活。他尽力复原3000年前最普通百姓的生活。在“居室”一节,他专门写到——小小土室,柴扉零落,用桑树的树干作为门轴,上面是草束覆蔽的屋顶,破了底的瓦罐放在夯土墙中,当作窗户,用破麻布和破毛毯塞在门缝窗缝里挡寒气……下雨天,屋顶漏水,地面也因为是挖掘在地面以下,进水是免不了的……在西周,大致是最穷的人,住这种半地穴的居室了。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叶超是许倬云谈话的朋友之一,他感受到,“他对于这些问题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一个历史学家去研究对象、一个考古学家去勘探文物的感觉,他是真真切切地去关心历史和历史背后或者历史中的这些人,这是他最关注的。”

笔耕不辍的不老学者
在2022新年谈话的视频中,许倬云提到,过去的2021年,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就是居然可以不疼痛了。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居然可以逐渐过比较正常的生活。
疼痛几乎是伴随他一生的阴影。许倬云出生时,母亲38岁,已经是高龄产妇,怀的又是双胞胎。在母体营养不够的情况下,强者取全部,弱者取其余。弟弟许翼云是健全人,而许倬云生下来就是伤残,肌肉没有力量,骨头没办法生长,一直到6岁都不能动。
8岁时,他自己发明一个办法,拖着竹凳子,一步一步向前移,后来才慢慢能站起来。这使得他从小就学会忍耐,在哪个角落都能随遇而安,有时在椅子里坐上一个小时,也得乖乖忍受,直到有人把他抱到别的地方。
家中兄弟姐妹都去上学,但他不能。后来,许倬云成为历史学家。身体限制了他,也给了他不同于其他人的视角,“我不能动,我是永远的旁观者”。
2021年,瘫痪之后袭来的疼痛,足足有3个月,那时,他已经疼到无法睡觉了。这样剧烈的疼痛,最后通过针灸才缓解下来。治疗的过程痛得死去活来,像潮水一样。这潮水哗进来,哗出去,绕着伤口这么转,真是浪潮一样。等那阵慢慢慢慢定下来,后来,居然可以不痛了。
令人吃惊的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中,只要他状况好转,就会让助手来家中记录自己的口述文章。他的脑筋一直在动,这个很惊人啊,九十几岁的学者,他不会甘心躺在那里养老,或者是消遣,什么看电视剧,没那个事儿,他就一直在思考。
葛岩是许倬云在上世纪80年代带的博士生,如今是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隔段时间,他会给老师打去视频,视频镜头中,他感到老师显老了,每次移动都赖于轮椅。
葛岩和妻子写信过去,请老师万万以健康为重。后来葛岩收到了老师的回信,那封信令他震动。老师的回信是这样写的:
为了做一日和尚,总得尽一日钟的责任,因此来者不拒,有人愿意听,我就尽力交流。毕竟,我们都是知识链的一个环节,这一长链,不能在我手上断线——葛岩,希望你也记得如此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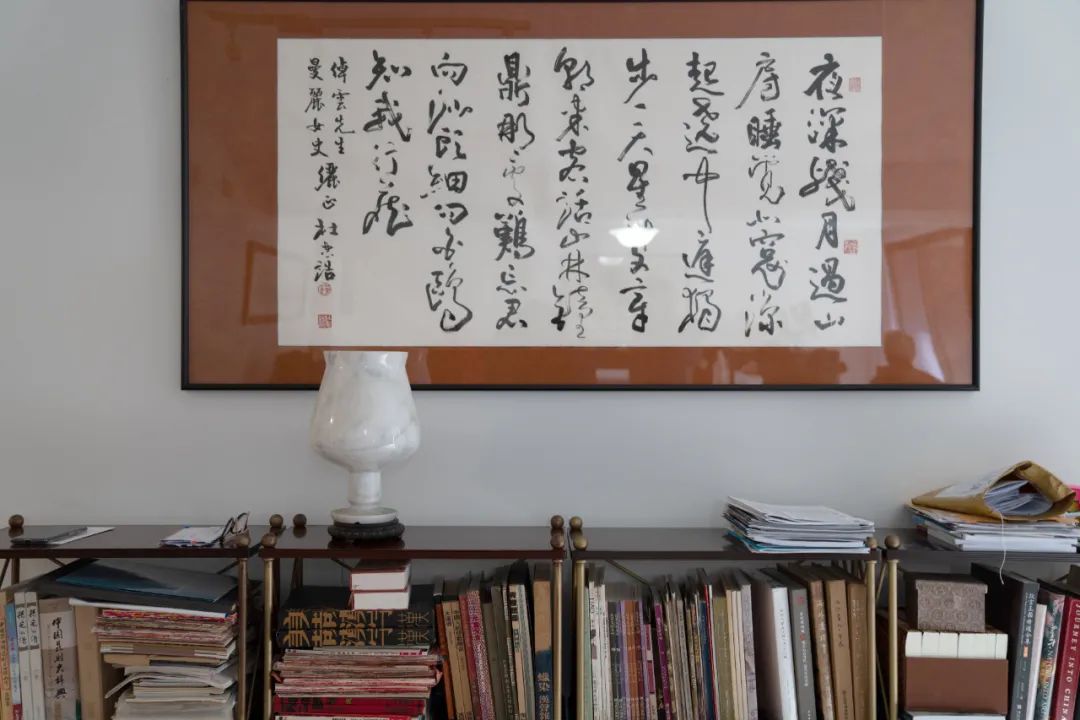 许倬云的书房一角
许倬云的书房一角
即使站在世界的高度,也保持聆听渺小的赤诚。有大学问的人,性格中总是混杂着悲天悯人和天真烂漫,穿过俗世的种种,你看到了他们的坚持,就有了继续下去的勇气。——小可
文本参考:
1、人物《许倬云——我跟大家共同努力的时间不会太长久了》作者:姚璐
2、许知远 《十三邀》
3、知乎 《许倬云:一个关于工作意义的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