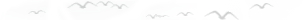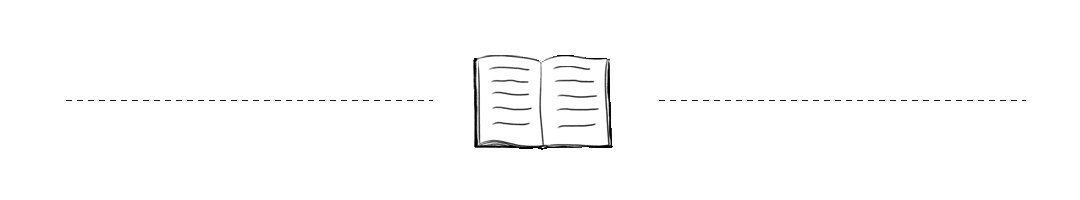遇见丨写了二十四年,我决定从头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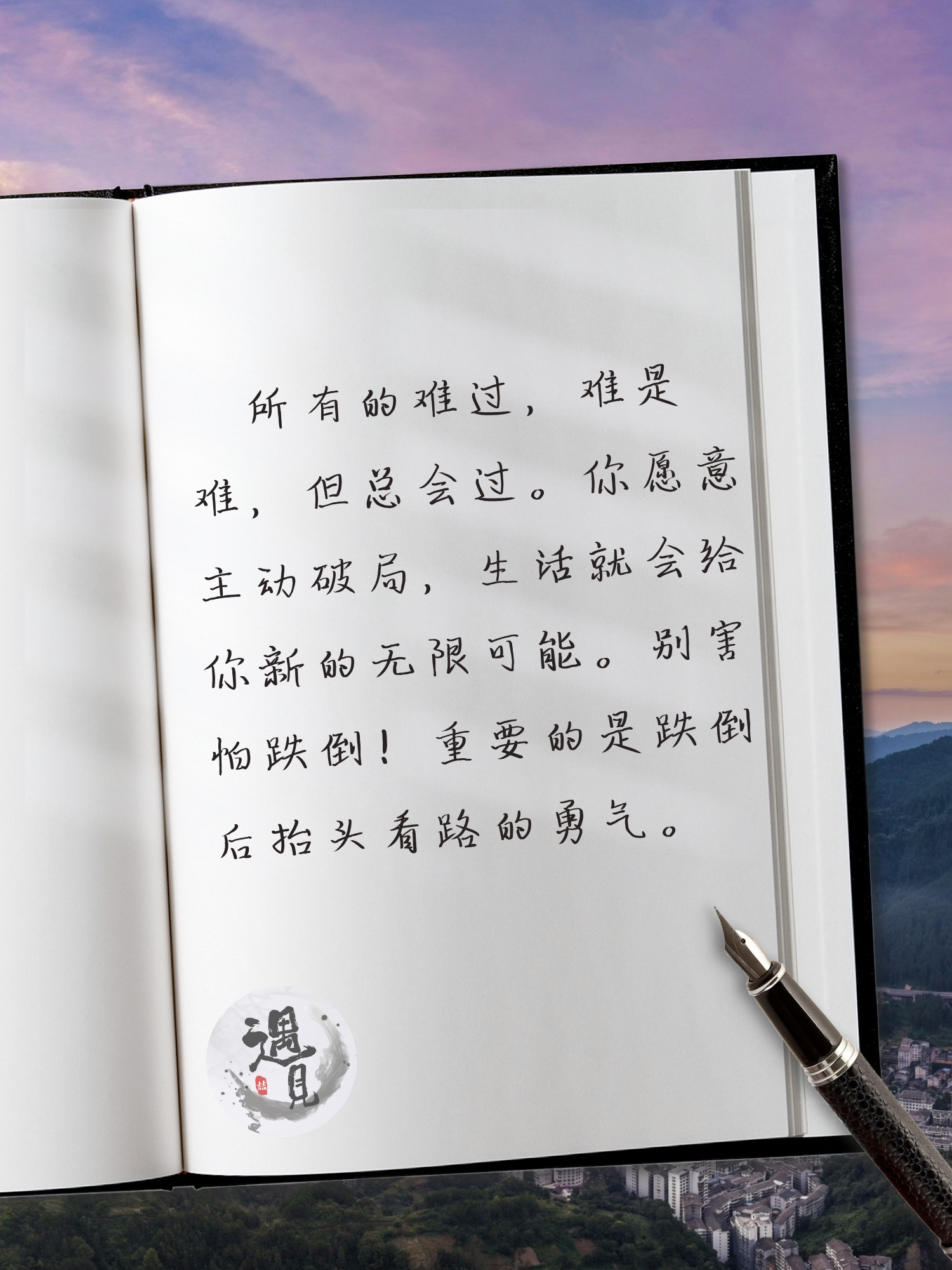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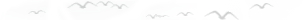
快递送到时,箱角被雨水浸湿了。我拆开它,里面是几本崭新的书:《电影剧本写作基础》《救猫咪》……拿起最上面一本,书页散发出油墨和胶水混合的、属于“开始”的味道。
对门的邻居老陈正好出门,瞥见书名,怔了一下:“老同学,我可是一路看你文章过来的。现在你主持不是挺好的吗,怎么想起研究这个?”我笑了笑,没说话。那本厚重的书在手里,沉得像一块砖。


晚上,合作多年的编辑发来语音:“帮我看看新稿子,就等你点睛了!” 我回复说,正在研究剧本结构。聊天框上方“正在输入”闪烁了很久,最后发来一句:“你都在台前站稳了,何必再钻回幕后从头学起?是不是太折腾了?”
手机屏幕暗下去的瞬间,客厅的灯亮了。爸爸端着水杯进来,看着我桌上摊开的书,轻声问:“听小陈说你要学编剧?当初让你学医你非要主持,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自己的节奏,何必再去当一个新手呢?”


那个晚上,我将那几本编剧书放上书架。它们立在我二十四年来积攒的各类文集和手稿旁边,簇新,扎眼,像一个冒失的闯入者。
是啊,有人二十岁就拿到了最佳编剧奖,有人写的网剧正在街头巷尾热议。而我,在面对“三幕剧”“情节点”这些术语时,感觉自己像个站在一年级教室门口的小学生,手里攥着的过往成绩单,全都失了效。
转机发生在上个月的一个行业影展。


茶歇区角落,我遇见了陆导。他以前是写严肃文学的,名声不小。此刻,他却像个学生一样,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分镜草图。
“五十二岁才想明白。”他抿了口咖啡,说得轻描淡写,“写了半辈子小说,发现故事还能用镜头‘写’出来。” 他告诉我,他的第一个电影剧本,被拒绝了十一次。直到第十二次,才有一位相熟的导演愿意坐下来和他逐帧地聊。


“所有人都劝我说,老陆,你写小说的就好好写小说,编剧是另一套语言,你学不会了。”他放下杯子,看着我,“但你知道吗?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恰恰是我写了几十年这个事实。我笔下的人物、对话、那些起承转合,它们不是没了,而是在我脑子里吵着要换个活法。”
他翻出手机里一张照片,是他家书房的角落:一个旧木箱里,堆满了这些年的手写笔记和打印稿。他拍了拍手机屏幕,“这是我的底气!三十多年的功底,它不会消失,它只是在等待一个新的指令。”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自己书房里那个类似的柜子,里面装着几百个人物小传,上千个故事灵感,它们像沉睡的士兵,而我,或许只是忘了如何吹响那声集结号。
影展结束后,我去小区门口的便利店买咖啡。老板老周,守着这店快二十年了。最近,他柜台角落多了台旧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总是些我看不懂的软件界面。
“在学剪辑呢。”有天深夜,我忍不住问起,他有些不好意思地搓着手笑,“卖了半辈子杂货,寻思给店里拍点小视频。”


我看过他拍的素材:镜头一开始总是晃得厉害,后来渐渐稳了;他学会了用特写展示面包金黄的色泽,用延时摄影记录深夜顾客的稀疏身影。他甚至给一包等待售出的香烟,配了段孤独的独白。
结账时,我说:“老周,你要是二十年前就开始学,现在肯定是高手了。”
他一边扫码,一边头也不抬地回道:“二十年前?我光想着怎么多卖几包烟了。但现在开始,明年这时候,我就是一个会拍视频的杂货铺老板。不也挺好?”


昨晚,我又一次站到书柜前。这一次,我没有看那些熟悉的书籍,而是打开了角落那个积灰的柜门。二十四年前的第一本笔记静静躺在那里,纸页已经泛黄脆硬。我小心地翻开,稚嫩的字迹间,赫然是几段笨拙的人物对话,旁边还用蓝笔画了个框,写着“场景:雨夜”。
原来,剧本的种子,在二十四年前的那个下午,就已经被我不经意地埋下了。
如果把二十四年积攒的人物、故事、悲欢离合,都放进这个叫“剧本”的新容器里;如果让那些在散文和小说里游弋的灵魂,找到光影这个新的归宿——那么,现在就不是一次狼狈的转型,而是一场准备了二十四年,蓄势待发的远征。


看,这就是我的开始。在写了二十四年之后,在一个最熟悉的地方,找到了一条最陌生的路。
而你的开始,可以在任何看似“太晚”的时刻,只要你还能听见内心深处,那声细微却从未熄灭的号角。
此刻窗外,夜正深。而新的故事,才刚刚拉开它的第一幕。
摄影/撰文:王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