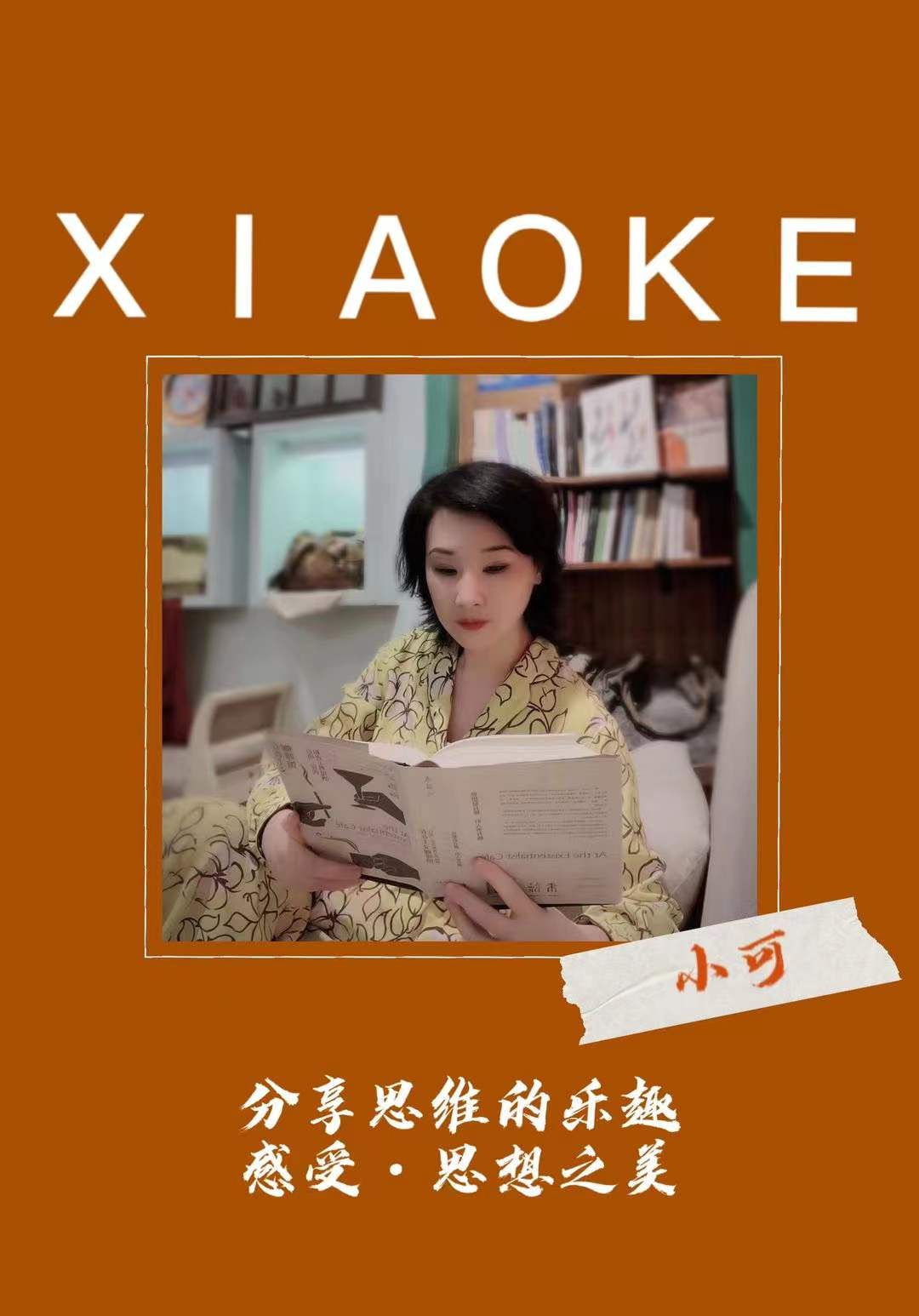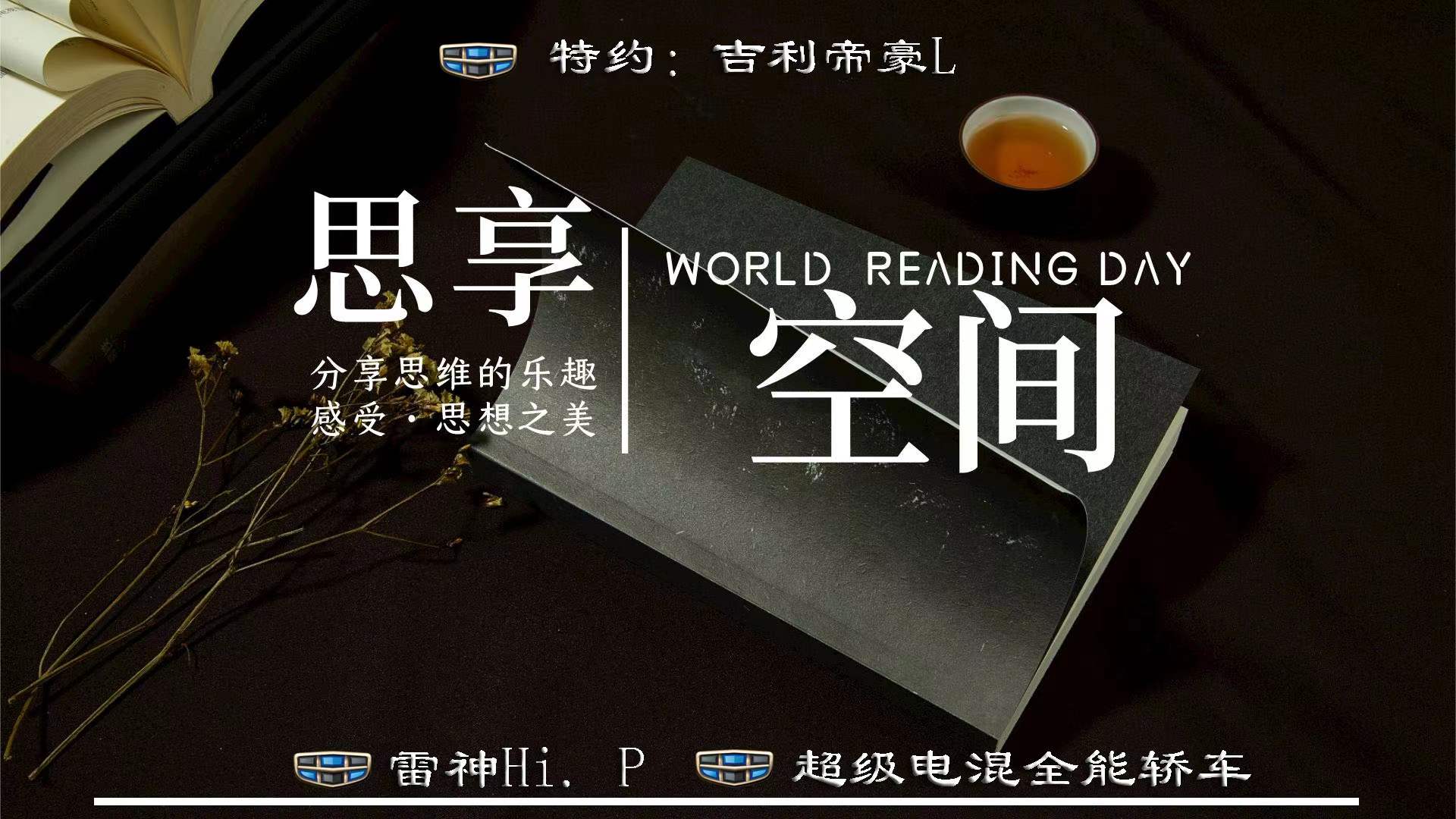思享空间·人物志|戴锦华——不变和任性可以走多远


戴锦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今年是她从教第40个年头。漫长的40年光阴中,高校的院墙,老师的身份,成全着戴锦华生活的相对平静。她的课堂,以电影作为切口,连缀起女性主义的前世今生以及全球化。
最近几年,经由网络,她的几门关于电影的课程被广泛传播,她也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所认识。在大众眼中,她始终是睿智的,有力的。人们发现,这位学者思考的领域如此开阔,不管面对什么困惑,似乎都可以寻找她,获得答案,也获得力量。
但是今年,生活对戴锦华而言呈现出不同的面貌。目光从眼前转向远处,一种一生中没有过的不确定感折磨着戴锦华,当一个有力的人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助,她能说些什么?

幼年时代,体弱多病,走在平地也能磕到门框一身青紫,同龄孩子无人待见,只能靠疯狂阅读填充童年的寂寞。12岁,身高超过一米七三,大人们在身后皱着眉头为她发愁。最终是疯狂的阅读解救了为自己的身高自卑的戴锦华。
有一年作为文学爱好者的父亲去香港出差,省吃俭用给她买回一本《简·爱》,读到简·爱那句“你以为我矮小、贫穷、不美,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少女的内心掀起一场海啸。她从此将这个19世纪英国荒原上的倔强少女引作知己。
她也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欣赏保尔而非冬妮娅,她为那种质朴的、燃烧一般的热诚而共鸣。直到现在她仍然承认,这本书,还在她的生命底层。
她身上,交织着“时代儿女”的壮怀激烈和不合时宜少女的敏感。1978年,她考入北大,大二大三时上过乐黛云老师的课。那时,乐老师和汤一介先生刚从国外回来,什么大件儿都没带,带回来的全是书,他们的家对年轻人完全敞开,许多人登门,哪怕是摸一摸那些书呢,但是戴锦华从来没去过。原因是“我根本没有勇气去敲老师的门。”
一个黄昏,她看见乐老师和汤先生在未名湖边散步,她远远地站住,看着他们走过去,看着他们的背影,看了好久。那个时候她就突然有一个特别明确的念头,就是要在大学里教书。“我要一生围绕校园,我要老了的时候像他们一样。”
“他们”是什么样?
就是那份安然,你知道他们经历过什么,眼见他们经历过什么,但是你看到那份无法被剥夺的精神的拥有,这样的人生特别值得。

1982年,北大毕业,戴锦华进入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当时同学的选择以报社、出版社为最佳,那是文科生介入现实的最好途径,学院则显得太封闭、离现实太远。但她坚持要做个老师。在电影学院,她总是穿长裙,戴长长的耳环,面容清秀,纪录片《彼岸》留下了她当时的影像——但这样一个女性,一旦说起话来,立刻显示出一种坚硬与笃定。她的语言具备某种召唤属性,钟鼓铿锵,汪洋恣肆,讲桌即广场。
到电影学院的第一年,在学校放映厅,戴锦华创造过一天连看11部伯格曼的纪录,在之后的生命中她重复过许多次与电影陷入热恋的故事。当时的电影学院位于朱辛庄的荒草丛中,正如电影学在国内也是一片空白。1986年前后,戴锦华向时任院长沈嵩生提出创建电影理论专业的构想,得到了毫无保留的全力支持。
学院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教师日日聚集在戴锦华的宿舍,重要的是业务讨论,初生牛犊的戴锦华经常跟周传基吵到脸红脖子粗,在这样的氛围中,戴锦华牵头建立起中国第一个电影史论专业。她事事亲力亲为,专业第一个班的招生,是她跑遍了全国各考区,一个一个面试挑回来的。遇到挫折,就去办公室找沈嵩生,拍桌子瞪眼睛。一种实干的浪漫主义精神充盈着她的青年时代,她梦想着建立自己的王国,世界是崭新的,她可以创造任何可能。
这种横冲直撞以27岁时的一场大病被按下暂停键,肺结核三期引发多器官衰竭,少女时代盼着小说女主角的悲惨命运落到自己身上,真的发生了,一点都不浪漫。在医院躺了八个月,从与死的贴身搏斗中,多少长大成人。进入90年代,一部分朋友出国,一部分朋友下海,那10年她感受到强烈的孤独,还有现实的困窘。
但她没有想过转换轨道。往后这些年,潮流又经过多少变迁,但戴锦华把一部分的自己永远封存在了她认定的年代。过了将近30年,在一场活动上为董秀玉颁奖,谈及董秀玉一辈的跋涉,谈及自己一生的选择,她借用《一代宗师》中的句子——大时代无非是一种选择,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时代。

1993年10月,受乐黛云老师的反复邀请,戴锦华返回北大任教。回去之前,她坦陈自己的所有顾虑:自己师出无门,学历又这么低,不想重新进入一个秩序中去。乐黛云说,我们有自己的小气候,在这个小气候里,保证你能够更好地发展。回北大不到一年,戴锦华去了美国,呆了一年多,这是她第一次有相对长期的国外生活经验。
上世纪80年代,乐黛云在国内开创了比较文学这一学科,任北大比较文学所所长,挂靠在中文系。1988年左右,由共同的朋友介绍,戴锦华成为乐家的常客。乐黛云从不掩饰对她的欣赏,在戴锦华任教北大后,从副教授升任教授举行的投票会上,因为一人未投票,没有达到全票通过的结果,一贯温煦的乐黛云发了脾气,摔门而去。乐黛云希望戴锦华参与管理,戴锦华说,她不愿。
那种不愿,其实就是一种任性。“我不耐烦,不耐烦经营一个机构、维系一个圈子所必须做的那些事情,我甚至就不耐烦养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对朋友,此生问心无愧,但是我不会去寄个贺卡啊,送个礼物啊,来养护这个关系,我们多少年不见面,见面的时候就是亲如手足,因为所有的好朋友都是出自相互由衷的欣赏,这样的朋友根本无需去养护,需要养护的大概就流逝了,太多太多的人就从你身边流逝了。”
她说:“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特别任性,我这辈子,特别特别任性。”

上世纪90年代初,她上过不少电视节目,有机会获得更多名望,但一次在餐厅吃饭时,被人认了出来。这之后颇长一段时间,她很少出现在大众媒体。一位男性朋友好心提醒,你跟某某起点一样高,如今他在不断升值你在不断贬值。
经常有朋友怒其不争,关系更好些的干脆说她愚蠢、冥顽不灵。每当这个时候,戴锦华都理直气壮,“我真心地说,他们为他们收获的东西付出的代价是我不想付的,也可以说是我付不起的。因为我要是付那个代价的话,我的生活也被毁了,我的状态也被毁了,我拒绝付那个代价。”
学生滕威20年前到广州教书,戴锦华叮嘱她,“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总有小狗跟在后面咬你的脚后跟,你如果停下来缠斗,你就留在这里了。要继续向前走,很快你就看不到它们了。当你进入了新的阶段,当然会有新一群小狗……”她对滕威分享了两则学院生存法则,一是老师这个职业一定要认真对待,二是尽早解决职称,这样你就可以做自己确信有价值的工作了。她自己也是这么做的。获得基本保证,然后任性。
这些年许多社会上的邀请、名流聚会,或者电影站台活动,戴锦华通常避之不及。但影展或电影节,或是创作论坛,她又一副义不容辞的架势。戴锦华习惯了用一种理想人格要求自己,或者是她已经成为一种理想人格本身。
戴锦华有个差不多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一回问她“你知道你很特别吗?”戴锦华跟对方开玩笑说,当然知道自己很特别。那位朋友否定了她的回答,“你不知道,就是因为大家小时候是一个样子,长大以后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样子,只有你从来没变。”可当她激怒了这位朋友时,表述就成了“说得好听是你有坚持,说得不好听,你就是一个偏执狂。”
任性和偏执,都需要付出代价。回首自己40年来的学术道路,戴锦华说起人生中一些失去,空间在失去,现场在失去,朋友在失去,甚至记忆也在失去。
一直到现在,戴锦华仍会在课堂上问台下的天之骄子们,酷暑的烈日之下,是否能够体认那些高温下谋生的劳动者?她用“体认”这个词,它是身体的,直接的,做不得假。
戴锦华说:“我一生为之自豪的东西就是,我基本坚持了我最初的信念,我最初那些最基本的原则始终没有改变。我憎恶不平等,我憎恶歧视和偏见,我憎恶恃强凌弱,我尽一切的可能和这种东西去抗争,并且坚持实践平等,我没有变过。”
与这种表达上的坚决相对应的,是戴锦华常常被外界忽略的一个特质——她经常处于一种徘徊之中。这种徘徊,构成了戴锦华的底色,她不是一个被观念所左右的人,她相信经验。戴锦华是有自我的人,她相信最属于自己的东西,也就是本真。她有一个本真性在那儿。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作为最早将女性主义研究引入国内的学者,近年来舆论中每每因性别议题吵得天翻地覆,戴锦华却有意压低了自己的声音。她不站队,而是发问:为什么经过漫长的反抗之后,只有性别议题硕果仅存?

在北大,戴锦华的办公室在中文系小楼的二层,在好几个有着中式红门的房间外,你很容易辨认出哪个是她的:门口有古朴的砖石地垫,窗内有猫玩偶,有插瓶的草花。这间小小的办公室,连沙发几乎都要被填满,她拥有无数小玩意儿,茶,咖啡,胶带,书,帆布包……每晚睡前的半小时,和很多想要放松的人一样,她打开淘宝,买些无用而便宜的小东西。
她有诸多无用的爱好,买精油,穿手链,甚至打造银饰。办公桌旁的墙上挂着一块软木板,木板上钉着打印出来的照片,作为一个女性,她喜欢把日子过得蓬勃而有琐碎的趣味。
此前多年,除了上大课,戴锦华还会组织自己的学生开设文化研究工作坊,2018年下半年的工作坊在中文系地下一层一间会议室里举行,时间是每周四的下午3点。进入会议室要穿过两道近乎20厘米厚的门,这里于是有了防空洞的气质。会议室有窗,但不开,外面是黑的,人在其中,隔绝了地面上的一切。
戴锦华总会提前一会儿到场,坐在前面的桌子旁,掏出保温杯。她有各种颜色的保温杯。她坐在那儿,笑盈盈地,看着到场的学生在两列相向的红桌子旁渐次排开。按照流程,一位同学会先就某个议题、某本书做报告,其他同学讨论,戴锦华随时加入其中,并在最后做出点评。按课表设置,工作坊应该在6点结束,但说到兴起,戴锦华会忘记时间。
她珍惜人与人之间的物理性相遇,就像她执拗地认为,不去电影院,就不算看过一部电影,因为人们聚在同一个空间内、让光束从身后打来,是电影这个艺术形式的应有之义。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她和当时一些肝胆相照的朋友聊起这个话题:什么是对你来说神圣的东西?她想了很久,最后给的答案,是尊重生命。那段时间,她在为《中国电影50部》备课,某天晚上,又重新看了一遍侯孝贤的《悲情城市》。
生命中闪耀的许多碎片跟重看《悲情城市》的感受形成了互文。片中主角一个个给朋友的家人送一封信,侯孝贤给了特写,接着闽南语的歌声响起,调子哀婉凄清。之后侯孝贤切换镜头,小上海酒家一切如旧,厨房里依旧在炒菜,全家依旧在吃饭,生活依旧在继续,活着的人继续活下去,活下去就是柴米油盐。
这次重看,戴锦华觉得这组镜头中有侯孝贤对生命的彻悟,侯孝贤喜欢远景和长镜头,渺远辽阔的《悲情城市》之中,这封信件是不多的特写之一。上面写的是——你们要尊严的活。

支撑我走到今天的是三个字,叫“我不服”,我不服,就是不论我沦落到什么地步,心里那个不服我是不放弃的。
——戴锦华
钢铁战士与少女情怀奇妙地融为一体的思想者、践行者以及一个毫不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她是个很大的能量场,有很丰沛的生命力和对生命的审美力。任性而自由、充盈而有力、不俗而诚恳。
——文郁
文本参考:《人物》——戴锦华 在场 作者:卢美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