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播州杨氏族属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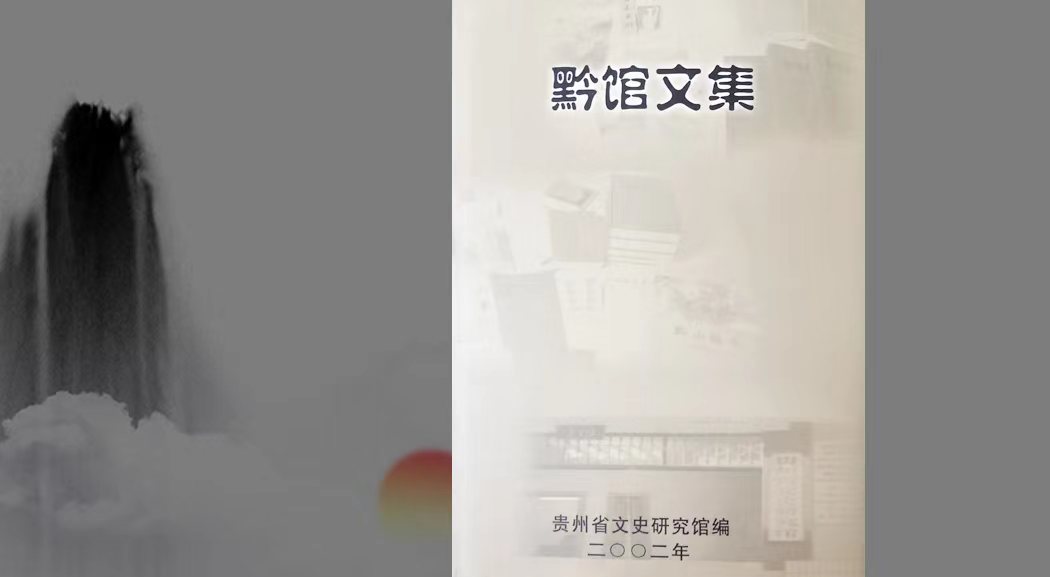
贵州遵义,古属夜郎范围。唐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置为播州。僖宗三年(公元876年),四川杨端应募入播平南诏,驻军高遥山,据险立寨,名所居为“白绵堡”,遂世有其地。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恭帝授铁骑左第二军都校马全义领播州刺史,后周亡,杨保才正式据有播州。杨氏盘据播州历宋、元、明三代,传二十九世,达八百年之久。播州杨氏究是何种族属,迄今尚无统一的看法。
1957年,贵州省博物馆在遵义县龙坪区永安公社皇坟咀发掘杨端十三世孙杨粲夫妻合葬基,出土了一批雕镂精湛的石刻及文物,为研究杨氏与内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杨氏的族属,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本文就是利用这些资料,结合历史文献,试图对杨氏族属作一初步的探讨。

杨端是播州杨氏的始祖。关于杨端的事迹不见于正史,要比较全面地研究他,只有更多地借助于私家著述。而这些私家著述,囿于各种不同的观点、立场,难免有褒贬失实的毛病。因此,在使用这类资料的同时,还须参以正史,择善而从。
《杨氏家传》(以下简称《家传》:“唐末,南诏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下诏募骁勇士,将兵讨之。”
公元八至十世纪,我国云南地区少数民族“合六诏为一”,出现了一个以白族、彝族为主体的地方政权——南诏。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51-754年)曾三次出兵攻打南诏,最后一次由侍御史剑南留后李宓将兵七万,深入至大和城,结果李宓被擒,隻轮不返。自此,南诏便摆脱了唐朝控制,不断扰犯边境。到季唐时,更为猖獗。懿宗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南诏派兵侵入黔中(今四川彭水地区),黔中经略使秦谋兵败,诏诛。播州于此时陷于南诏。
杨端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募入播州的。《杨粲墓》出土残墓志铭:
“▢▢▢▢▢▢▢▢▢▢▢▢▢▢蜀无壅塞之患,而六诏绝▢▢▢警。”
这是歌颂其始祖杨端平南诏有功之辞,可以印证杨端这一人物存在的历史事实。
《家传》:“端与舅氏谢将军,诣长安上疏请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诣泸州、合江,径入白锦。”
这段话透露出了一点杨端籍贯、族属的信息。为什么说“行次蜀”呢?“次”有止息、止驻之义;同时,“次”是指止息在三日以上的时间。具体地点,是泸州、台江,关键在一“诣”字。泸州、合江固然是由蜀入播必经之地,为什么不说“经”,而下一“诣”字?须知“经”是一过了之;“诣”有到、至之义。“诣泸州、合江”是有所事事。我们可以这样设想:杨端与其舅氏谢将军到长安应募请行,当然不敢领军同行,待在长安得到了朝廷允许后,返回蜀地,再“诣泸州、合江”组织、动员义军就绪,才“径入白锦”。沪州、合江一带地区,正是古来僰人聚居的犍为郡。《说文》:“僰,犍为蛮夷。”汉时犍为郡领有十二县,其中僰道(约今宜宾)、江阳(约今沪州)、符县(约今合江)、资中等七县皆在蜀地。据此,我们就可推断,杨端带入播州的是僰人部队,而杨端本人是僰人中的大姓领袖。
上面提到的“舅氏谢将军”,是一个探索杨端籍贯、族属的重要线索。《华阳国志·南中志》:“公孙述时,三蜀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境,闻世祖在河北,乃远使使番禺江出,奉贡汉朝,世祖嘉之,号为义郎。”三蜀是蜀郡、广汉、犍为三郡的统称,从上引可以知龙、傅、尹、董、谢诸姓,都是蜀中大姓。谢暹在此志中,书出全名、职称,而其他四姓只有姓氏,名职全无。道理何在?原来两汉制度,州、郡主官,有权在所辖区内辟除属吏。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则往往是在大姓中征辟。谢暹就是此类被辟除的大姓属吏。“功曹”一职,位虽不显,毕竟是朝廷命官,他与一般少数民族大姓,自然应有区别,故特举其名姓、职称。这种笔法史中多见。大约在东汉初,谢氏有部份族人迁入贵州,成为后来的“牂牁大姓”。一部份仍留居蜀地,谢将军很有可能是三蜀谢暹的后裔。在古代崇尚门第的社会里,杨、谢结为姻亲,想不会是偶然的。两家的民族族属和居住地点,当不会相离太远,估计总是叙府、泸州、合江一带的僰人地区。
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引《南齐书·氐杨氏传》称:“蜀杨之先出于氐”,认为:“播州杨氏固氐族,”这个论点很有道理。不过“氐”所指,太觉笼统,还得加以分剖。古人往往把氐羌连称并举,一般常误会是两种不同的民族。实际上“氐羌”是一个同义并列词组,“氐羌”即羌族,《诗·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不来享。”传:“氐羌,夷狄国”,释文:“西方夷秋国。”羌是我国西北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以羊为图腾,以教畜为业的游牧民族。殷时与殷人战争频繁,羌人战败被俘,常被用作祀神的“牺牲”,或论为奴隶,此多见于殷代卜辞。后来出于种种原因,一部份羌人南迁,进入四川,逐渐向南转移。他们的后裔分布在西南广大的地区,繁衍日多。早在春秋战国时代,羌人的后裔就到了云南益州生息。南迁的羌人,经过长期地与当地民族融合、分化,又形成了新的氏族部落,从而随着出现了不同的民族称谓。僰人就是从羌人分化出来的,两者有着很深的血缘关系。《史记·司马相如传》《集解》引徐广曰:“僰,羌之别种也”可证。汉代的著作中,常将“羌、僰”并称,如扬雄《长杨赋》:“羌僰东驰”,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潢中羌僰”,还;有《汉书·伍被传》《扬雄传》皆有“羌僰”一词,可见汉人尚知羌僰同源。“羌僰”又可作“氐僰”,如《后汉书·杜笃传》:“捶驱氐僰”,可见氐、羌是一种民族的两种称谓。
据此,“蜀杨之先出于氐”,就可以说是“蜀杨之先出于羌。”那么,蜀杨是羌的后裔无疑,当然是僰人了。《贵州通志》认为播杨来自蜀地,这一论点是很正确的,只是没有把氐的来源弄清楚罢了。

播州杨氏有“杨业后裔”一说,信着颇众。《家传》:“贵迁太原人,与端为同族。宋赠太师中书令业之孙、莫州防御使延朗之子充廣,尝持节广西,与昭通谱,昭无子,充廣以其子贵迁为之后。自是守播者,皆业之子孙也。”顾炎武《播州志》亦主此说,所不同者,“充广”只作“充”。《关西杨氏族谱》:“杨端,授武略将军,诰封太师宣慰,五传至昭无子,以延朗之孙,充广之子,贵迁为后。”《唐史》不见有“武略将军”之职,“宣慰”乃元实行土司制之官,可认为是元代追封。《宋史·杨延昭传》:“延昭本名延朗,后改焉,……录其三子官,其常从,门客亦试艺叙之,子文广。”延昭三子,除文广有传系于延昭后外,其二子因如常人,故不书其名职。如真有子充广“持节广西”,官与父相等,何以失载?《宋史》为元脱脱主纂,号称精审,何致疏漏如此!或曰,充广是文广之误。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文广从狄青征侬智高,为广西铃辖,知宜、邕二州。《家传》说:贵迁要“报国自效”,特上书“请缨”,由播州出兵“助讨”,此明言贵迁是早已在播州,不然何能出兵“助讨”。
再考皇祐四年,距延昭死已近四十年,延昭卒于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五十七岁。古人早婚,二十或二十五生子,此时文广已年近七旬。又杨昭立于宋初,推其年龄当与延昭上下,又何能与文广或充广通谱?“业之子孙”的说法,值得怀疑。
播州杨氏与中原杨氏确有交往,但不是杨延昭之子,而是另一个人,时间也早得多。

早在春秋时期,僰人已和汉人有了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秦时已经在僰人地区置吏,进行统治。因此,僰人的汉化程度较其他少数民族为深,上层人士还读孔孟之书,并且还被政府辟除为吏。历史上一直认为僰人是:“夷中最仁,有仁道”,而“语言最正”的民族。播州杨氏可以说是僰人中汉化最深的代表。据载,杨氏统治播州时期,原是很注意“文治”,“闻四方有贤者掇厚币罗致之”,由于杨氏“留心艺文,蜀士来依者甚众”。杨氏“建学养士,大修先庙”,完全是模仿汉人的一套统治方法。《杨粲墓》的形制、规模与中原,尤其是四川内地如出一辙,是很可以说明问题的。
《杨粲墓》是一座仿木建筑结构的双室石墓,其墓葬风格与内地汉墓同,但还具有本民族的特色。特色之一是佛龛式的布置。棺室正壁用石仿建筑结构刻制而成,主龛重簷垂脊,顶置火珠,垂脊上饰以蹲兽,两端鸱吻双翘,散斗双阑,抹角𣟚柱,完全合乎《营造法式》“佛、道、寺、观”的款式。龛中置杨粲袍服冠带,袖手端坐圆雕石刻像。左右两旁各置侍童一身,有如“胁侍”。龛位层阶中央刻有佛教符号,枋柱下端有放光宝瓶图案,阶下两旁又置裸身赤足,披片趺坐的高浮雕负重力士二。庑壁间还置有浮雕文官、武士立像,两两相对,共四身。这种手法完全是佛教摩崖式样,说明墓主生前是一个笃信佛教的佛教徒。
少数民族中有无信仰佛教的呢?有的,僰人就是很崇信佛教的。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十:“阿缚(通僰)喜通佛老”;田汝成《炎徼纪闻》:“僰人,今普安州,……其人喜佛事,男女手数佛珠”等,就是证明。僰人也称白人,故风俗“与南诏同”。《资治通鉴·唐纪》六十八,载高骈守蜀,与南诏谈判,因“国人好佛”,特派僧景仙为使,后南诏酋望赵宗政来请和亲,要求“为弟不为臣”,态度骄横。崔澹怪罪高骈“不识大体,反因一僧咕嗫卑辞,诱致其使。”可知僰人崇佛不自明清始。
《杨粲墓》又有一特点,是在夫妻两墓室的腰坑中出土了两面铜鼓。铜鼓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特有文物,凭此就可以排除杨粲是汉人的可能性。铜鼓是西南少数民族的重器,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宋史·蛮夷传》:“相攻击鸣鼓以集众,号有鼓者为都老,众推服之。”《明史·刘显传》:“……鼓上者,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可见少数民族对铜鼓的重视。宋王朝为了达到羁糜的目的,特“诏释黄铜禁”以示优渥。
铜鼓并非少数民族皆有。费孝通在《贵州少数民族调查》一书中说,铜鼓是由木鼓演变而来,是早期僚人的葬具,所谓“鼓葬”。苗族也宝爱铜鼓,但皆得之于田间地下,非其所铸。这种说法,已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明。1972年,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在修筑晒谷场时,发现一处用铜鼓作葬具的西汉少数民族葬墓。葬法是铜鼓口部对扣,尸骨用“珠襦”包裹,置于鼓中,属二次葬。有人说是僚人的“竖棺葬”,盖富者用铜鼓,贫人则“刳木为棺”。
除僚人外,经地下发掘证明,僰人墓葬也用铜鼓。1957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发掘了一处古墓群,在大墓M1、M23两墓棺下腰坑中,共出土五面铜鼓,有的底部尚留有烟炱痕迹。它很像殷周时代中原人的“鼎”,是煮肉的用器,又是象征权力的重器。楚雄古名威楚,是僰人聚居的地区,万家坝的古墓群是僰人的墓地。《杨粲墓》的铜鼓在墓中方位与万家坝一样,都是在腰坑中,说明两者出一相同的族源。
《杨粲墓》的铜鼓,有一鼓鼓侧尚残留有“元祐通宝”的钱币残角,这很值得注意。“元祐通宝”是北宋哲宗时所铸,流行于两宋,说明铜鼓是用当时通用的钱币铸造。想是铸鼓时匆忙将钱币遗漏在鼓范中,才会有此现象。因之推想,它是赶制来作重器入葬,否则不会制作如此粗糙。入葬非用铜鼓不可,这就反映出杨粲的族属,僰人的特点。
作者介绍:

章光恺(1933-2001),贵州贵阳人,著名画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生前主要从事文物书画鉴定和书画创作,精于古文字学,对史学方志也有研究,在明清史和贵州古代史研究上,有很多独特见解。其书画作品除国内收藏外,深受东南亚各国收藏家的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