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凤头、猪肚、豹尾——谈诗词的起承转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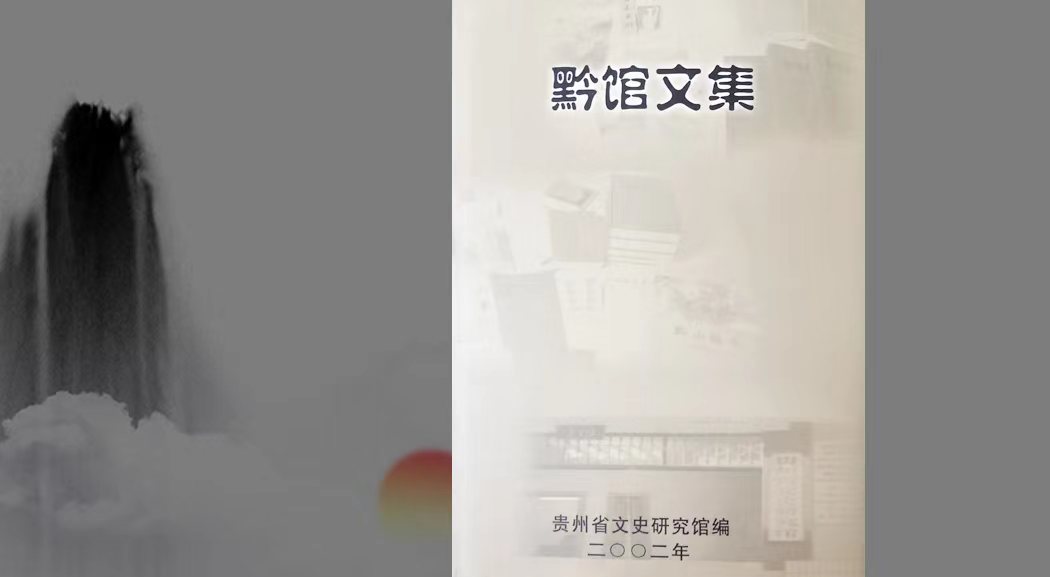
成功的诗词作品,除有好的立意、意境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适度的剪裁,精心的安排,严谨的结构。就是说,要在起、承、转、合上下一番功夫。如何开头、如何承接、如何转折、如何推进、如何收尾、何处伏笔、何处照应、何处点题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使其“首尾圆合,条贯统序”。
元朝人齐梦符对诗词结构作了形象的概括,他说:“作乐府亦有法:曰凤头、猪肚、豹尾六字是也”。这里所说的乐府,是泛指诗歌词赋,也可通用于一切文艺创作。这“六字真经”,可视为诗词结构的基本法则。
前人把诗词结构分成开头、承转、结尾三段,我们按“凤头”“猪肚”“豹尾”的顺序来谈谈起、承、转、合。
一、凤头
“凤头”五彩缤纷,飘逸秀美。诗词的开头要象“凤头”一样色彩鲜明,引人入胜。俗话说: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诗歌的开头怎样的才算好?怎样才能达到“凤头”的标准?手法可以说是多样的。
一种是“突起法”:大刀阔斧,开门见山,落笔入题,势如奇峰巨浪,给人兀突雄劲之感。如杜甫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一句亦为全诗题旨。起笔流畅自如,表达了久经战乱、流落异乡的杜甫,忽听到官军收复失地,由极悲而极乐的感情。带出了下面的喜泪盈眶,漫卷诗书,放歌纵酒,作伴还乡的一连串动作和“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奇妙想象。这些,全是由开头的“忽传”二字引起,感情炽烈奔放,一泻千里,不板不滞,被后世誉为“天下第一快诗”。又如李白的《蜀道难》这一千古绝唱,亦复如此。“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一声惊叹,奇境突出,造成了不可仰视的势态,形成了振聋发聩的力量。全篇主旨全在一个“难”字上,以下笔墨全都环绕“难”字着力。
“突起法”也就是“造势”的开头。这种起法有几个特色:一是“高唱”,调子高、感情浓,造成新奇别致的格局;二是意境深,角度高,极尽苍苍茫茫之致;三是几突诡谵,像高山坠石,不知其来,完全出人意料之外。故在历代诗词作品中,此种起法较多。
一种是“平起法”:由远及近,由淡而浓,如电影中的淡入,又如小溪流水,潺潺而至。作者为抒写情怀,咏叹事物,并不直抒心臆,而是触景生情,情寓景中,“一切景语皆情语”,写景为了写情。通俗地说,就是托物言志,借题发挥。这种手法也叫“造境”的开头,在诗词创作上最为常用。
杜甫的《春望》更是造境开头的典型。题为“春望”,望到的并不是春光中桃红绿柳,水秀山明,而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一景语道尽了唐朝经安史之乱后的破败荒凉的景象,景中深深地寓着诗人感时伤世的沉痛心境。接下去便是更为悲凉的感受,“感时”“恨别”,花也溅泪,鸟也惊心,烽火连天,家书隔绝,白发蓬乱、疾病缠身,这一切都是在“国破山河在”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
不同的人写同样的景,由于诗人的感受和心境不同,览物之情悲喜各异。有“感极而悲者矣”,也有“其喜洋洋者矣”,这也是很自然的。同为描写秋景,范仲淹的《苏幕遮》以“碧云天,黄叶地”开头,因诗人欲抒发孤独的羁旅思亲的情怀,写的是寂寞凋零的深秋。而辛弃疾的《水龙吟》则以“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开头,写的是水远天高的清秋,正好表达了诗人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
一种是“设问法”:欲擒故纵,巧造悬念,设问入题,这是一种“造思”的开头。这种开头,由作者提出问题,又由诗人自己逐步回答,像导游一样,使游人渐入佳境,往往能收到出奇制胜,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设问法”在诗词作品中虽不多见,但仍有不少名篇力作。
最有名的要算杜甫的《蜀相》,“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还有李白的《大雅久不作》,“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以上这些开头,或因景而问,因事而问,因人而问,因情而问,首句或首联往往成为全诗的总目。诗人发问之后便立即作出回答,以后则层层引入,环环紧扣,造成一气呵成的势态。
“设问法”的开头,词中似比诗多。它可以用来抒发豪迈奔放的情感,劈头一问,如钱塘潮涌,山口风来,收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如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感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开头设问之后,又问“今夕是何年”,再问“何似在人间”,还问“何事长向别时圆”。最后,诗人出来总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表达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的良好愿望。一问到底,一气呵成,如大河奔流,波澜万顷。
设问开头也可以用来描摩细腻复杂的景物,抒发缠绵婉约的心境。冯延已的《蝶恋花》中就有几首是以设问开头的,“谁道闲情抛掷久?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烟恼韶光能几许? 肠断魂销,看却春还去”。问得深沉,问得悱恻,问得哀怨,似听到诗人的声声慨叹,使人荡气回肠。
二、猪肚
“猪肚”是要求诗词的体干内蕴丰厚,容量充实饱满。诗词的体干部基本由承接、转折两部分组成,承接开头,转入结尾,把诗意向深处更开掘一层,推进一步,避免平铺直叙,使诗的内容、意境再突奇峰,再涌波澜。既要使之与开头相呼应,又要使结尾收得住。具体地说,要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诗的承、转具体部位。律诗一般是指颔联(第三、四句),颈联(第五、六句),有时也包括第二句和第七句在内,这要看诗的具体而定。绝句一般是二、三句,二句是承,三句是转。
承:有紧承、反承、隔承法。
紧承就是依照开头的原意紧紧承接,没有停顿,没有留下间隙,没有终止感。
如杜甫的“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李白的“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等,承接句无不从开头句引发而来,意思紧接,形象连贯。这种写法在诗词最为多见。
反承:承接句与开头句的诗意、形象完全相反,似是有意出现拗句,出现停顿,留下空隙,自身已形成一个转折,且为下面的转折留下伏笔。这种写法在诗词中并不多见,但往往收到腾挪迭宕的奇妙效果。
如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虽是从“一岁一枯荣”句衍化而来,而此联自身已形成了一正一反,使之迭出波澜。
转:有正转、逆转、急转。
正转是转折部由承接部顺势发展而成,与开头、承接部份在诗意和感情都未发展,未成转折,这种写法较为容易。但在艺术上却往往失之平庸与堆砌,除非有警句警语补救。
如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飞流直下三千尺”“孤帆远影碧空尽”和苏轼的“欲把西湖比西子”等等,都是顺转。诗意上是连贯的,形象是完整的,只是或总收,或提炼,为收尾留下更多的空间。
逆转是转折句,与承接句完全相反。山重水复、顿生奇境。使其波澜起伏、摇曳多姿。
如鲁迅的《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来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颈联与颔联的意思变化很大,“破帽遮颜”“漏船载酒”,这里虽含满腔悲愤,但也有无可奈何的嘲讽。而颈联则是“横眉”“俯首”,爱憎分明,诗句警策,似在低吟中一声长啸,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一联表明了诗人对敌我的态度,形成全诗的主题。
三、豹尾
豹尾是讲诗词的结尾要挺拔俏丽,或精策,或雄豪,或淡远,总要给人留下回味的余地。古人说:“一篇之妙在乎煞尾”,所以,我们作诗填词对结尾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结尾就是“起承转合”的“合”,也是“收束”的“收”。根据诗的内容不同,自然有不同的结尾法。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说:“收束或放开一步,或宕出远神,或本位收住”。这里讲的都是从题目说的,一种是就题目从本位收住;一种是从题目宕出远神;还有一种是就题再放开一步。
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中,就写作技巧也归纳了几种结尾法。像李白《听蜀僧浚弹琴》,“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听琴听得出神,不觉天已近暮,用的是衬托手法。杜甫《春宿左省》,“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明朝有本章上奏,夜难入寐,几次询问更点,用的是借事抒情手法。杜甫《房兵曹胡马》,“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是用议论作法。章承庆《南行别弟》,“万里人南去,三春雁北飞。未知何岁月,得与尔同归”,用疑问作结,反映不得同归的离情。张九龄《自君之出矣》,“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以比喻作结。储光义《江南曲》,“日暮长江里,相邀归渡头。落花如有意,来去逐船流”,用写景来抒情,并寄托含意。李白《越中怀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宫殿,只今惟有鹧鸪飞”。三句说盛,结尾说衰,构成反衬作结。贾岛《渡桑乾》,“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无端更江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两用并州,首尾呼应,用推进一层手法作结。杜牧《过华清宫》,“长安回望秀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用画龙点睛手法作结。李商隐《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两出“巴山夜雨”,后者是想象的,用想象以抒情作结。这里就提供了九种结尾法。
从意境上讲,还可分为高收、淡收。高收是讲角度高、境界高、手段高;淡收是讲结尾淡远,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诗词是创造性的形象思维活动,并不为章法所囿,以上讲的全是“死法”。在我们创作过程中,每人可根据自己的感受,结构出不同的方法来。陆游在《文章》诗中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作诗贵在情趣,贵在自然,不可雕章琢句,强自为之。但要懂得章法,认真结构,才能写出真正的好诗来。
作者介绍:

韩乐群(1933-2015),湖南常德人。国家一级编剧,诗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著有大型声乐作品《雷锋组歌》《遵义大合唱》,出版有歌词专集《山里山外》,诗词专集《刺梨蓬草》,创作电视剧《两家春》,歌剧、黔剧《瓦窑寨》,儿童京剧《长发妹》等。曾任《中国对联集成——贵州卷》上卷执行副主编及编辑部主任,搜集贵州省明清以来各类对联1200余则。为贵州音乐事业和地方文化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