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丨论郑珍诗歌的艺术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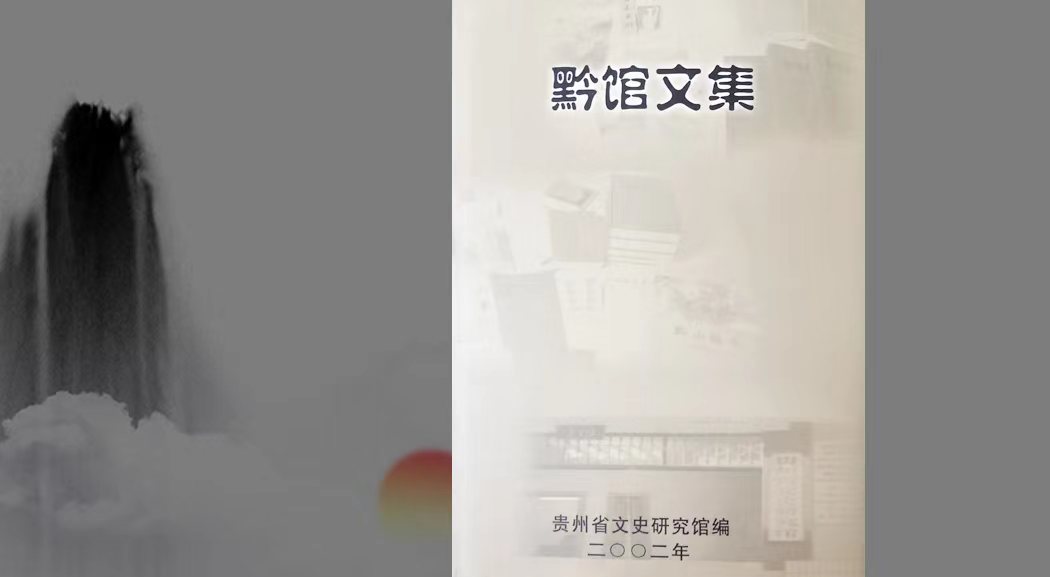
清代晚叶,生长在贵州的郑珍,以《巢经巢诗钞》和《后集》跻身诗坛,被推尊为“有清一代冠冕”的诗家。仲联先生评巢经巢诗为“清诗第一”。郑珍诗歌风格独特,引起研究者们的兴趣,提出了多种见解。如莫友芝的“隽伟宏肆”说,陈夔龙的“奥衍溯懿”说,陈衍的“生涩奥衍”说,黎庶昌的“瑰奇孤邈”说,翁同书的“简穆深厚”说,陈柱的“深厚渊奇”说吕廷辉的“平易”说,黎汝谦的“质而不俚、淡而弥真”说,刘大杰“横恣俊峭”说等。近人胡先骕提出郑珍诗多用“白战之法”,即白描手法;缪钺先生也认为郑珍诗多是白描。
上述诸家所论,各照一隅,都难以概括郑珍诗歌的总体风格。其中,“奇奥渊懿”说一向被认为是巢经巢诗的基本风格,影响较大;但“淳厚平易”说也为不少论者所首肯。这两种绝然相反的风格在郑珍诗作中具体表现如何,二者能否辩证统一?郑珍诗歌风格形成、发展和变化情况怎样?多重风格与总体风格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很值得探讨。

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既与诗人性格志趣、生活境遇、艺术追求密切关联,也与他所承袭的文学传统、时代风尚,文学潮流相关。通读郑珍诗作,不难发现其晚年风格与早年迥然不同,与盛年诗也有差异。其诗歌风格的发展变化,大约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
郑珍青少年时代不仅熟读经史,对历代名家诗作学得也很用功。他“溯骚赋汉唐而下诸大名家,靡集不窥;择其尤脍炙者汇钞成册,含咀有年”(郑知同《子尹府君行述》),善于采撷百家,“转益多师”,艺术风格因而丰富多姿。“早年胎息眉山,终模韩以规杜”,醉心于苏轼纵横恣肆和黄庭坚奇崛峭拔的诗风,对韩愈雄放奇奥的诗风尤为景慕,钻研韩诗达30年。因此,郑珍青年时代诗作的主导倾向是攀奇逐奥,浪漫主义色调较浓。如《浯溪游》描绘浯溪奇特景物:苔蹬、檈桥、樟木、峿台、摩崖……用奇幻的笔墨,渲染出奇崛峭丽的意境。当登上峿台颠顶,俯视万丈深的“窳尊”,但见“尊中凝脂白如霜,疑是元子残酒浆”。诗人奇思联翩,“奇景”与“奇怀”交融,铸成瑰伟奇幻的境界,透发出诗人昂扬奋发的情思。
郑珍35岁以前的诗作,如《留别程春海先生》《招张子佩》《郡教授独山莫犹人先生七十寿诗》以及《玉蜀黍歌》等,或学术渊源,或考作物来历,旁征博引,文词奥博,确是“奥衍渊懿”之作。这时期的诗歌,除奇奥峭折这一风格外,也还有淳厚自然、清新艳丽的作品,待下面再论述。

中期的诗歌,主要是从35岁到49岁之间,即从郑母去世到就任荔波县学教谕之前的作品。母亲溘然长逝,郑珍心绪与志趣大变。回顾生平,虽然饱读诗书,具有“下笔如奔川”的才华,但科场不利,五试“秋闱”才中得举人,两试“春官”均名落孙山,未讨得一官半职,穷愁境遇没多大改变。曾两次游幕,因“强于腰,讷于口”,见不惯官场尔虞我诈的丑态,不愿置其中。此时,他心灰意冷,置丙舍于墓侧,读书其中,有终老林泉之意。为哀悼,三年辍笔不作诗词。除服后写了《四哀四首》《和渊明饮酒二十首》等诗,寄托怀母之思,抒写悲愁情怀。后一组诗中描绘了“脱命鹿”的形象:
喘喘脱命鹿,自伤五岳姿。回忆向来路,环身戈戟枝。斑雏角茸茸,骨相何清奇。苹蒿不自饱,衔与尚尔为!
这正是郑珍身世的自我写照。几十年坎坷生涯,他对人生、世情的认识和体味比青少年时代深得多了。反映民间疾苦、抒发个人悲苦情怀的诗歌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内容更加深刻,感情也更为深挚淳厚。如《系哀四首》中《双枣树》一首写道:
晚凉朝露午晴天,柳阴藤荫藕香边。有时阿母来小憩,有时阿母还留连。挲挲挽挽挠捻管线,续续抽抽纺木棉。紫薤堆袍帮妇脱,黄瓜作犊与孙牵。一案鸡乳呼齐至,五色狸奴泥可怜。当时家计诚贫薄,母身虽劳母心乐。……
这是一幅劳作行乐图,母氏音容行止宛然在目。事隔三年,“而今陈迹浑不存,空有破亭留枣根”。全诗处处流溢思亲深情,悱恻诚挚,比早年思亲的诗作更深沉、更凄苦,形成酸涩苍郁的特有风韵。
这种酸涩苍郁的诗风,还表现在一些描述友情的作品中,如《石头山歌送郘亭还郡》抒写送别挚友莫友芝的情怀。诗中写了红桂、黄叶、夕阳、彩霞、碧潭、游鱼,描绘一幅绚丽多彩的秋烟送别图。这一对科场不利、仕途失意的老友,在夕阳秋风中话别,更增添了无限的愁绪。虽强颜为笑,但送别的低沉歌声却掩不住内心的凄苦。诗人以华艳富赡的笔致来抒写沉挚绵缠的别绪,另有一种深沉苍凉的情韵。这种寓酸楚于华赡的艺术风格,正是酸涩苍郁风格的发挥。这种风格的形成,与诗人学习孟郊,受其濡染相关。

郑珍的后期,即颠沛流离时期的诗歌创作,大部收集在《巢经巢诗后集》6卷中,即从49岁到59岁(1954-1864)的作品。这正是西南各族人民在太平天国运动推动下,掀起反清大起义的时期。郑珍在起义军冲击下,东躲西藏,贫病交困。他一直未改关怀民瘼的初衷,写了许多反映民间疾苦,揭露官府兵练和土豪劣绅罪行的诗篇。
郑珍认为自己作诗是“粗服乱头,自任其性”,要求“言必是我言”“我吟率性真”。由于他性格诚朴,对亲人、师友和受苦民众充溢着一股孝慈诚笃之情,发之于诗,情真意挚,质朴自然,毫无矫饰造作之感。这类诗作早期、中期都有。郑珍晚景凄凉,对民间疾苦体验更为深切,诗歌的内容更为充实,感情也更为深厚。又兼晚年诗艺更为精进,不惟各体皆工,而对很难做好的五七言古体尤为擅长,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晚期反映贫窭生活的诗,如《食老米》《家米至》《断盐》等,不仅描写了个人的苦况,更表达了对贫苦劳动者的深切同情。如郑珍在府城任书院讲席,每月薪俸只有陈糙米一斗,要养活一家十口,该有多么艰难!但他吃着糙米饭,想到的是家乡人的处境:“艰难当此时,发我乡人慨。家家人字棚,坐地枕锄耒。人多野蔌少,日或一顿菜。惨闻食糠饼,哽涩入喉内。得此我何幸,虽粗亦聊赖。惜只四日粮,愁到空釜对。”(《食老米》)全诗文字平易朗畅,不用一典,纯系白描,而情感如此深挚,胸怀如此宽阔,深得杜、白诗歌的情韵。
形成这样的艺术风格,自然离不开语言的因素。郑珍诗歌语言运用有两个主要特色:一是力争句法的变化,一是善于吸收民间口语俗语。
在句法方面,常使用杂言句式。除五、七言外,还用了三言、四言、六言、八言、九言、十一言,甚至有长达十六言的。如《吴军行》中一小节写道:
小儿或触已裂旗。谓儿裂我旗,缚儿儿乱啼。将军怒詈命斩之。十金到手,云儿无知。
四、五、七言参差运用,错落有致,不仅生动活泼,韵味掌也极隽永。
其次,打破了五、七言的内部结构程式,推陈出新。如“携小妹共载”“要唾尽始快”为“一二二”式;“炊或不及焉”为“一三一”式;“他日更借人乘之”为“二三二”式;“承以瓶盘桶罂缶”为上二接下独立五字。这类例句不胜枚举,变化多端的句式,结构活泼,表意自如,使声律更富于抑扬跌宕之美。
以民间口语俗语入诗,如“庙成鬼老待何年”“猫翻甑盎狗饮饫多”“事既少见多所怪”“天生菜园肚”“鸡飞狗上屋”“徒苦脚板皮”等等。通俗生动,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一种天然浑朴的美感。

郑珍诗歌风格还有宏肆、诡奇、艳逸、清丽和诙谐等多种侧面,显示了丰富的艺术志趣和高超的艺术才情,这里不一一论述。就其早、中、晚三期不同的艺术风格而论,早期的奇奥峭拔,中期的酸涩苍郁,晚期的淳厚自然,既有差异,也有关联;既相互对立,又辩证统一。
早期受韩、苏、黄等汪洋恣肆、瑰伟奇崛诗风的熏染,但并非生硬剿袭,而是融进质朴的因素而自标一格。程千帆先生指出,"郑子尹学韩(愈),却以朴实教韩的险怪”,很有道理。即便在奇奥峭拔的风格中,也隐含着淳厚的因子。中期的酸涩风格中,更见出淳朴真率的素性。晚期的淳厚风格,不仅是酸涩的深化,也隐透出刚硬峭折的骨力。胡先骕称巢经巢诗“以苏、黄、杜、韩之风骨,而饰以元白之面目”,颇有见地。钱仲联先生说:“子尹诗盖推源杜陵,又能融香山之平易,昌黎之奇奥于一炉,而又诗中有我,自成一家而目。”郑珍诗确能融各家为一炉,铸成自家独特的风格。这种风格到底是什么?能否用简炼的语言加以概括?
就以前各家的评论来看,都只是标明郑诗风格的某个侧面,不足以概括其总体风貌。笔者试用“淳博峭丽”四字来表述郑诗的总体风格,意在突现其“淳厚”“酸涩”的主要特色,也包孕着渊奇、峭折和清丽、自然的因素。“淳博峭丽"的风格,是郑珍“悃款朴忠”品格的自然显现,也是他渊博的学识、超迈的艺术志趣与坎坷的人生际遇相互融汇而凝成的结晶。这种蕴含着“酸涩”情味的艺术风格,也是时代风潮的产物。郭绍虞先生曾说:“当时海禁已开,国家多故,具有敏感的文人更觉前途的暗淡不安,于是言愁欲愁,其表现力量,也就更能深刻而真挚。黔中诗人莫友芝、郑珍,尤足为代表。姚永概《书郑子尹诗后》云:‘生平怕读郑莫诗,字字酸入心肝脾。’在这种诗格中,也直觉谈神韵谈格调皆无是处,即侈言性灵,如与随园一流之矜弄聪明者,也大不相侔。”可见郑珍诗歌的艺术风格,同时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风貌。
作者介绍:

黄万机,生于1935年,贵州遵义人,著名学者,遵义沙滩文化研究专家。代表著作有《郑珍评传》《莫友芝评传》《黎庶昌评传》(三书曾被湘潭大学采作硕士生必读教材)、《沙滩文化研究文集》《贵州汉文学发展史》《近现代诗》选注等,点校整理古籍《黔南丛书》诗歌卷、《郑珍全集》(300多万字)等20多种。长篇传记文学《普通一兵——记“文化将军陈沂” 》纳入解放军元帅将军传记回忆录丛书,获中国作家创作成果金奖。


